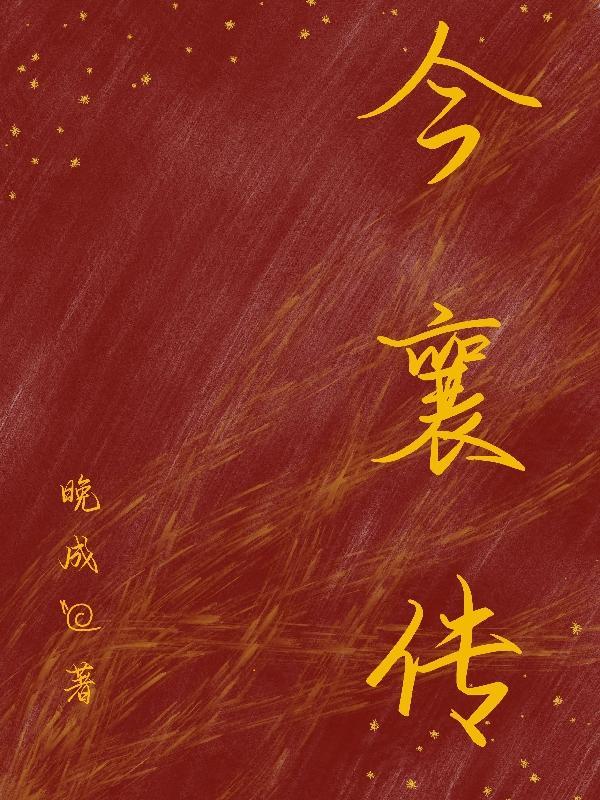69书吧>绽放的花朵图片 > 第12章 深海朝圣 6(第4页)
第12章 深海朝圣 6(第4页)
kam咔哒咔哒地吐了吐舌头。“天哪,你真是瞬间杀手,苏。”
“你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说。
“那你的理论是什么?”
她问道,身体前倾。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已经进来坐下,面对面地坐在圆圈里。通往这个区域的平台消失了,让我们“被困”
了,我心中闪过一丝焦虑。
“嗯,先,如果他们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为他们在整个旅程中所做的一半事情而烦恼呢?”
我问。“为什么要把我们和男孩们分开?为什么费了这么大的劲,让我们在马车里看不到我们要去哪里?
“嗯,显然他们不可能让我们知道去这个地方的路,”
她说。“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可以稍后再回来,再次施放异常占卜至宝,弄清楚我们到底被送到了哪里。”
我抿了抿嘴唇。“这可能是真的。但它只解释了其中的一半。为什么一开始就要爬上以太桥呢?
“可能只是一层额外的混淆,”
她说。“让外人更难猜到去哪里看。”
我皱起了眉头。这是有道理的,但我无法摆脱我在这里错过了什么的感觉。就像一颗松动的牙齿,在我脑子的角落里唠叨。。。。。。
“你知道,”
奥菲莉亚说,来回摇头,“从中心看到这幅壁画是这样的。。。。。。真的很漂亮。
我环顾四周,模仿她自己的动作。正如她所说,在这个位置上,壁画有一些我以前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从门口看它。它在房间的曲线上挥作用,具有流畅的品质,以一种几乎有点催眠的方式将您的视线从一个元素引导到另一个元素。设计的流动性质使图像感觉像是悬浮在水面上,你的眼睛随着它的流动而移动,一圈又一圈。。。。。。
在这个地方奇怪的气氛中,在黑暗的石头和我们脚下不可能看到的景色的映衬下,它呈现出一种几乎凡脱俗的品质。就像我几乎可以坠入丰富的彩绘色彩中,就像我可以跌落到下面的大6和海洋一样。
我浑身抖。这里很冷。结界一定是在做些什么来保暖,因为我们并没有被大灯之外的虚空的极度寒冷冻死,但仍然有一股寒意穿透了我厚厚的骨层。那是一种干燥、刺骨的寒冷,就像夜幕降临后的沙漠一样。
“它到底是什么?”
kam说,看着自己。“恐怕我不太明白。这些设计太抽象了——我想那应该是一艘船。。。。。。?
我也不太清楚。我能辨认出一些场景。一个男人在哭泣,有人潜入水中,一座高耸的城市在地平线上。。。。。。
“我也听不懂,”
我说。“不过,我认为它试图讲述某种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说?”
kam扬起眉毛问道。“这些场景在我看来无处不在。”
我摇了摇头。“不,肯定有某种叙述。有一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男人正在从水中出来。。。。。。然后他就把自己弄干了。。。。。。也许吧?我眯起了眼睛。“至少,它有结构。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
“有意思,”
卡姆说,她的表情变得更加好奇。“为什么命令会把这样的东西放在这里?”
因为这里有人觉得这个信息是最重要的,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在想,我模糊地认为它位于逻辑和情感推理的交叉点。他们相信这是他们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每次进入圣所时都需要提醒的事情。一个真理,比其他任何真理都更珍贵。。。。。。
不,这是不对的。
我感到寒意第二次袭来,还有另一种冲动。这是所有声音中第二安静的;一个甚至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就看到了事物的人,在梦的逻辑边缘徘徊。也许这是表面的目的,但仅此而已。这里没有真正的真理。
我只看到,有那么一瞬间,笔触很锐利。在颜色的对比中,一种微妙的仇恨,在表面之下酝酿。我看到这个人的手在他们画画时,编织着流动的色彩线条,并想象着他们计算设计时脸上一定挂着的苦涩的冷笑。蔑视,创造表面的美来掩盖更深层次的丑陋。在更短暂的时刻——当我脑海中的联系火花四射,疯狂地伸出手时——那天,我看到了我祖父眼中平静的厌恶的表情。当他最后一次去参加秘密会议时。。。。。。
不知怎的,我知道这是真的。
不管是谁做的,都是轻蔑的。这是一个安静的笑话。
值得嘲笑的东西。
“这太可恶了,”
我大声说。
冉冉猛地朝我的方向转过头看了一会儿,似乎被这句话弄得措手不及。她眨了眨眼。
kam也看了看。“那是什么,苏?”
她问。“你刚才说这很可恨吗?”
“呃,我不认为这是可恨的,”
奥菲莉亚说,用一种令人惊讶的防御语气,因为她只是在大约3o秒前才成为这幅壁画的粉丝。“在我看来,它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