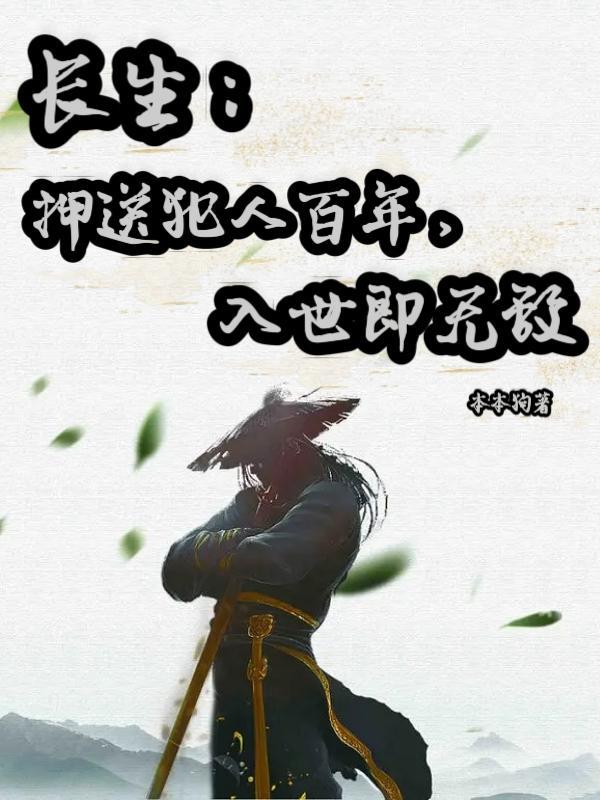69书吧>清白的梦破了是什么歌名 > 阴天(第1页)
阴天(第1页)
在南方待久了,染上了喜欢雨天的毛病。这病又有病根,短时间看来是很难治好的。
我逢人便说,也在好些文章中提到了我的这个爱好。有没有引起共鸣暂不知晓,也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不可耐烦。但在我的心里,甚至觉得说得不够多,写得不够多,恨不能无远弗届。
自从回到故乡来,面对更多的是阴天,而不是雨天,这有些差强人意。
在阴天,看见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来去去,我打心里开心。可是偶尔也会奇怪地想到:若是在他们身上加上一点忧郁的气息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种忧郁来自于自然、人物、故事均可,这样他们的思考会不会更有深度呢?我不是什么名人,没有求全之毁的顾虑,自然能够坦言自己的想法。我更不是九斤老太之类的人,不会觉得一辈不如一辈,反而我特别羡慕他们、相信他们。就我的年纪本应该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的,但是对于时间的流逝和年华的荒废却深有体会,有时候懊恼到悻悻然不知所措的地步。
在阴天想到这些,实属必然。
自入五月以来,似乎没有见到过万里无云的天空。每天清晨醒来,窗外的榆树总是低垂着。灰蒙蒙中,偶尔让我觉得它不再是榆树,而是漆身吞炭为一尊披着绿衣的塑像,没有丝毫活气,这让本就安静的清晨不是在报太阳的即将到来,而是在报黑夜的刚刚远去。大有弋人何篡的架势,我又能奈之何?
在小楼的顶上,之前时能看到一群鸽子忽而落下,忽而飞起,像是点缀着一些花绣。现在回想起来,竟不知已有多久没有看到它们了,这让我十分诧异。很久以来,我都用心地以知音的身份去看待一些除人之外的事物,并从中获得快乐。聊胜于无,也乐此不疲,这比人与人之间的繁文缛节来得更加容易,更加真切和信服。
在阴天体会到这些,实属必然。
对于我来说,阴天绝无野叟献曝之嫌,而是行探骊得珠之实,它预示着雨天的到来。等啊等啊,雨来了,洋洋洒洒,花草尽情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人们撑出各色的伞,在伞的边缘,流线的雨水和伞拼组出一座座小小的蒙古包,使人的心神飞往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云蒸霞蔚,再无尘世的烦恼。在花园中,时时传出的唼喋声,是雨的声音还是鸽子的吃食声呢?
当然也有等不来雨的时候。据我的观察,阴着的天空并不是灰色一片,而是云彩们有大有小,有高有低,颜色有浓有淡,搀扶着、相拥着……它们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聚在了一起。如果是因为爱情聚在了一起的,如果它们有语言的话,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我想起一诗来: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
一会儿云层中透出来的几丝光,一会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像是来偷看大地的一样。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多云的天气。在这种情况下,在云彩和雨之间,我更想将“云彩”
比喻为母亲,将“雨”
比喻为子女。当然这样的比喻有些个人主义的偏颇。那些偶尔探出的阳光,是云彩派来观察人世间的善恶的。它对自己的孩子给予了极高的期望——润泽山川。
在阴天憬然有悟,也实属必然。
这是阴天的幸运还是我的幸运呢?这是它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吧。浮一大白,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