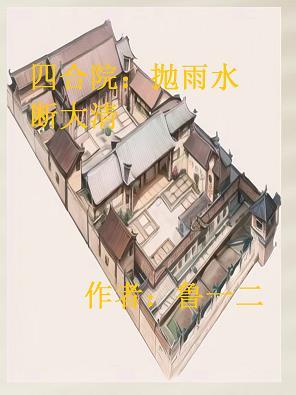69书吧>九重阙定方和长公主 > 第52节(第1页)
第52节(第1页)
大不了就去御前打官司,看到时谁更丢脸。
更何况,风重华又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单只看她处理文氏的事情即可知。既然已打定了主意,文谦便不再将安陆伯府放在眼中,只等着风重华守孝结束。
到夜里,文谦领着一家人回了府,这才将文氏的事情说给周太太听。
周太太乍听之下固然是吃惊,更多的却是欢喜:“妹妹没事就好,只是不知道现在安顿在何处。”
文谦并不回答她的问题,反而与她说起了家常:“你可还记得前几月,华姐儿向我们借了几千两银子?”
他这么一说,周太太顿时怔住了,蹙眉道:“老爷的意思是,几个月前华姐儿就开始谋划此事了?”
文谦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青瓷茶盏,一团白雾自茶盏中升腾起,映得眼前的人都有些模糊:“如我所猜不差,约是从那日她们母女被赶出府后便开始了。”
谋划了这么久,可他们却直到文氏死亡一日才知道。这番缜密的心思,这番的胆大包天,令周太太背上升起一层虚汗。
“可现在圣旨已下,若是让圣上知道?”
周太太悚然一惊。
文谦抬眸,目光落到妻子身上,眼波微闪,“说不得要借琦馥一用了。”
“什么?”
周太太没有听明白。
文谦笑了下,身子向后靠了靠:“阿福,你老实与我说,琦馥是不是不想去辽东?”
他这么一说,周太太的脸腾地红了下来。
周家男丁兴旺,女儿运却艰难的很。周太太是她那辈唯一的姑娘,而周琦馥却是这辈中唯一的姑娘,怎不如宝如珠?上至老祖宗,下至各房兄嫂都爱护备至,可也养成了她泼辣蛮横的性格。
“还不是她那个爹,若不是他,琦馥能跑到京城来求我?”
周太太矢口不提琦馥的错处,先把帽子扣到她弟弟身上,“辽东苦寒之地,他一呆就是数年,居然还将琦馥也叫了过去。定岳就不说了,那是儿子吃苦受累应该的。可咱们琦馥自小娇生惯养的,何必吃那苦处?莫说是她,换做是我也不去。”
周太太睨了一眼文谦,将手里的青瓷茶盏重重地放到桌子上。其实,周克令周琦馥去辽东还有另一层用意。他看上了山东布政司王真的公子,想结秦晋之好。可是周克之妻鲁氏却有忧愁,她担忧一旦周府与王真结亲,会引来永安帝猜忌。便向周太太送了信,请她在周琦馥入京之后加以拦阻,不许她入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