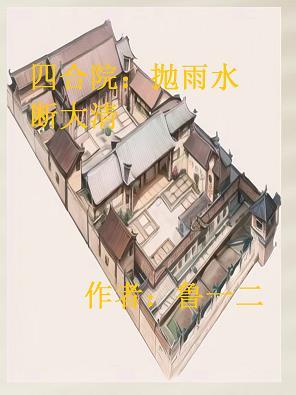69书吧>一程山海一路繁花 > 第4章 调包谜案2(第1页)
第4章 调包谜案2(第1页)
夜已很深,万恒呆坐在花棚中,花棚的灯光将万家小院涂上了一层哀伤的光晕。
万恒的妻子饶静霞躺在床上,她已在生命之苦的重击下,毫无抵御地倒下。万嘉卉坐在一旁,给烧的母亲换着冷敷的毛巾,懵懂而倔强地守护着。
万恒独自坐在花棚里,看着花棚里的花、满架子的种子,自己拍摄的野生花卉照片,以及多年积攒下来的花卉资料……看似漫无目的,但其实他是在搜寻,搜寻那些此刻可以抓住,能让他的灵魂再次坚强的依靠。
但搜寻良久,他的眼里依然是绝望和哀伤。
二百多万的花款,四十多位花农一个季度的收入。花农们起早贪黑,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手上划出血痕,一次次结成硬茧……这些钱挣得多不容易呀。想到这些,万恒就感到心碎。
如果这些血汗钱找不回来,无论如何也得给花农们一个交代。可是,怎样交代?万恒心里没有任何思路和办法。但他知道,不论是周宝明还是赵太,都能找到逃避责任的理由,唯独他不能,他必须给花农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明月村花款调包案,一传十,十传百,持续酵,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成了明月镇的头条新闻。就连昆明市的几家报纸也都登载了这则社会新闻。
很快,村子里不知从哪里传出了流言蜚语,传闻万嘉卉的父亲万恒,就是那个暗中做手脚,让花农的辛苦血汗钱打了水漂的幕后黑手。
传闻像迷雾一样扩散,蔓延开来。
万嘉卉所在的明月中学,也被传闻迷雾所包围,下课间隙,学生们也都在谈论这蹊跷的调包案件。
万嘉卉被同学指指点点,心理压力已经到了极限。每当下课,她索性避开所有同学,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
这天,万嘉卉正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树下呆。
赵太的儿子赵鸿运、周宝明的儿子周光远、赵鸿运的表弟王大河,都跟万嘉卉同级,但不同班。赵鸿运、周光远、王大河与几个常混在一起的男生议论着花款被调包的事情,故意来到了万嘉卉附近,还提高了声音,生怕万嘉卉听不到。
“你们想想,全村二百多万的巨款。二百多万啊,就在她家丢了,谁干的?”
赵鸿运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地讲着,眼神瞟向万嘉卉:“说不清道不明,我爸那是痛心疾啊!”
“怎么回事?这事现在都传疯了。快说说。”
一个同学故意让赵鸿运继续讲下去。
“警察还在找证据,但基本上能够肯定就是那人干的!”
赵鸿运背对万嘉卉,向身后翘起大拇指,指向万嘉卉的方向:“这事就是秃头虱子明摆着呢!”
周光远拉了一下赵鸿运,示意他适可而止。但赵鸿运却不加理会。
王大河使坏的小眼神滴溜溜转,继续火上加油:“这么多钱,可是要判刑的。”
异样的眼光,充满恶意的喧嚣议论,如毒雾弥漫在万嘉卉的周围。
万嘉卉感觉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她相信自己的父亲,父亲绝对不是别人口中的监守自盗者。父亲是一名高洁的鲜花护卫者,怎么会做出这样低劣的事情?!她无法忍受别人当面抹黑自己的父亲。
万嘉卉起身,走向赵鸿运,赵鸿运他们一时愣住,都瞪着眼睛看着她。
万嘉卉走到赵鸿运跟前:“赵鸿运,你我都不在现场,都没看见生了什么。警察还没有公布调查结果,你就这样说,就是血口喷人!”
万嘉卉把“血口喷人”
这几个字说得一字千斤重!
万嘉卉的好友丁勇志、张灏来找万嘉卉,隐约听到了万嘉卉的话,于是,快步走了过来。
走到跟前,张灏看着赵鸿运和周光远提高声音道:“赵鸿运,你们说话都注意点,你爸、周光远他爸也是押款的,你们怎么不说呢?!”
“你这是什么话,我爸又没拿钱啊!”
赵鸿运涨红了脸反驳道。
“你爸没拿钱,你怎么知道别人拿钱了?”
丁勇志也立刻加入了辩论行列。
赵鸿运支支吾吾辩驳:“我说的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的话,就要有证据。你爸要有证据,就应该交给警察。如果没有,你这就是诬陷。”
万嘉卉有理有据地反驳赵鸿运。
“你当然要为你爸说话了。”
赵鸿运涨红了脸。
“我以事实说话,我爸不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