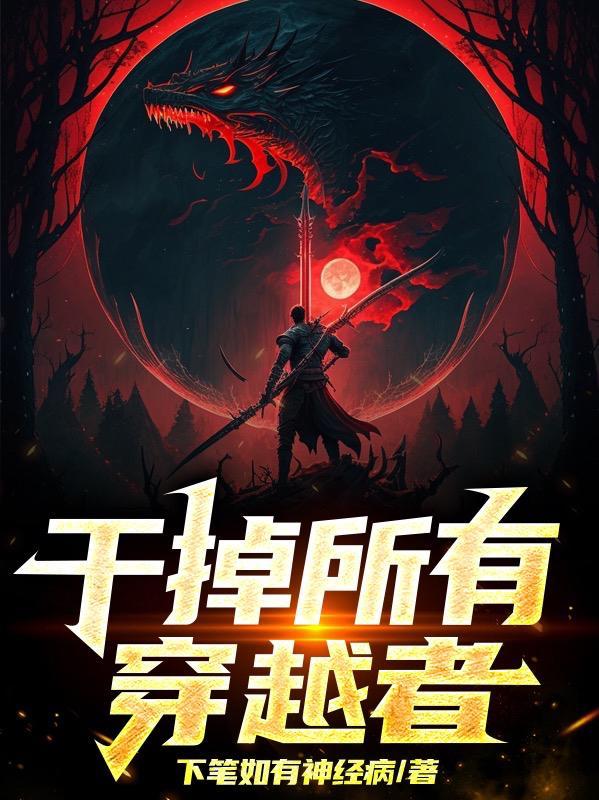69书吧>小侯爷那么 > 第18章 谁是恶人(第3页)
第18章 谁是恶人(第3页)
“油?”
李弦玉听闻沈桥舟的话,把苹果滚过的痕迹都摸索了一遍,果然在桌子最里面现了黏黏糊糊的油迹。
丫鬟们都是常年打扫厢房卫生的老手,不可能留下这么明显的错误。预定厢房的贵人们锦衣绸缎,身上更是一丁点灰尘都没有。
唐婉婉是舞女,方毅是书生。
心里愧疚的小侯爷听到对话后,堵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能找个地方扔出去泄一番了。
“走吧,张金山家。这次看看他还有什么想说的。”
张金山家就在在东市一个偏僻的胡同里。等江问清他们赶到时,那斑驳掉渣的墙壁上已经挂满了白色的丧幡。
崔思昂询问住在门口的街坊邻居。
“这张金山家生了什么事?”
“婆娘死啦!说来这张金山也是可怜人。闺女头两天因病去世,这婆娘禁受不住打击,一口淤血没有吐出来,硬撑了几天没撑住,也跟着一块去了。”
旁边一个花袄的老妪搭腔:“那闺女是婆娘难产生下来的,晚来得子,宝贝得紧。谁知道短短几天双双撒手人寰了,只留下这么一个糙汉子,日子可怎么过呦~”
风吹动一缕缕烛烟,也吹起地上白花花的纸钱。张金山跪在灵堂里,曾经宽阔挺拔的脊梁一时显得尤为落寞。那一瞬间,本来质问的话语成了四方的沉默,凝聚成一团巨大的怜悯,重重的压在每一个人的胸口上。
江问清等人默默地拿起一炷香为亡者悼念。祭拜完后,沈桥舟将满是油污的衣物找了出来,李弦玉闻后确定跟万嫣阁三层地板上的油渍一模一样。
“别费力气了,是我干的。”
张金山缓缓起身接过衣物,生怕此等污浊脏了他人的手。
“这个女人害我家破人亡,我做鬼都不会放过她的。”
“说说吧,你那天都干了什么?”
“唐婉婉把我们一家子当猴耍,结果女儿病情复,生命垂危。孩子她娘接受不了这个消息,也跟着一起去了。”
张金山语气哽咽,很难想象堂堂七尺男儿竟然哭得泣不成声。
“案当天虽不该我排班,但是我又回了万嫣阁。我准备去后厨拿菜刀找她拼命。厨房向来人多嘈杂,根本不好下手。所以我就空手去了唐婉婉的房间,可惜她并不在。我又打听到这个女人上了三层,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众人心里都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该不会这么巧吧~
“嘿,那个女人跟狗一样,腹部捂着一把刀就往外爬。你们看看她到底伤害了多少人,是个人都想杀她!她看见我想求救,求我救救她。当初我跪下求她救救我女儿时,她那副丑恶的嘴脸呢!我一脚就给她踢回房间了。她身上的伤是我打的,这是老天爷赐予我的机会啊。”
“唐婉婉有罪应该上报衙门,交于官府处置。你又凭什么自诩正义的代表来审判他人生死。”
“我早年走镖干了不少偷鸡摸狗的事。金盆洗手后,又帮唐婉婉做过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天道有轮回,或许这就是我张金山的报应吧。”
“再有什么话,去大理寺里说吧。”
张金山老泪纵横,紧紧抱起两个牌位,跟着崔思昂和沈桥舟一步一蹒跚地往大理寺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