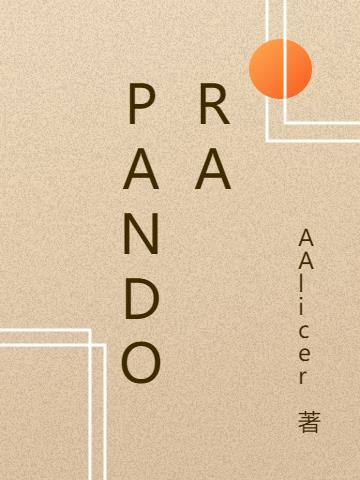69书吧>宝宝什么时候断米粉 > 第25节(第1页)
第25节(第1页)
不能怪延王爷。
鱼玉春本身就没什么存在感,还没被抄家,实在无法引人注目。
延王爷想了想说:“皇兄移驾的时候,他没有跟着走,不是屈服于韬王的淫威,就是人头落地了吧。怎么?宣府与他有交情?”
仆人说:“鱼侍郎是我们家小二奶奶的父亲。”
连个名字都说不清楚,用“有几分姿色”
来形容的父亲吗?
延王爷原本懒得管别人家的闲事,却觉得小二奶奶兴许可以拉拢过来,便问:“小二奶奶是哪一位啊?”
仆人说:“是小二爷的夫人。”
“……我见过吗?”
“您抄家那一日,正好是她嫁进宣府的日子。”
延王爷:“……”
一听“抄家”
两个字,就觉得一口鲜血从胸腔冉冉升起。
流放之地,通常都天高皇帝远。京城打得热热闹闹,岭西依旧平平静静。
延王爷睡了一觉,推窗见山,忽感岁月静好,光辉荣耀如昔日烟云,消散远山的晨曦之中,心中生出疑问:
我是谁?
为何在此?
将来如何?
“王爷。”
侍卫敲门,将他拉回现实,“皇上送来密旨。”
延王爷打开门,指着床边的大箱子:“念完就丢到里面吧。”
离开京城之后,皇帝就在路上养成了有事没事写张密旨的习惯。开始还会诚惶诚恐地跪接,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反正十有八九都是“早安”
“晚安”
“野花真美”
“路人真丑”
的问候和感慨。
侍卫不是第一次干这大逆不道的事儿,驾轻就熟地读起来:“吾弟安否?一别数日,甚是挂念。昨夜起风,一地残叶,独看无趣,待你归来,共赏之。思你,念你。盼你归来。”
延王爷:“……”
一地残叶,独看无趣,难道两个人看就有趣了吗?不还是一地的残叶吗?
侍卫将密旨放进快要溢出来的箱子中。
延王爷纳闷地说:“没了?就这样?”
侍卫说:“圣驾已经到了合邕……”
延王爷瞪了他一眼,摆手说:“此处人多耳杂,小心为上。去宣府投拜帖,再探探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