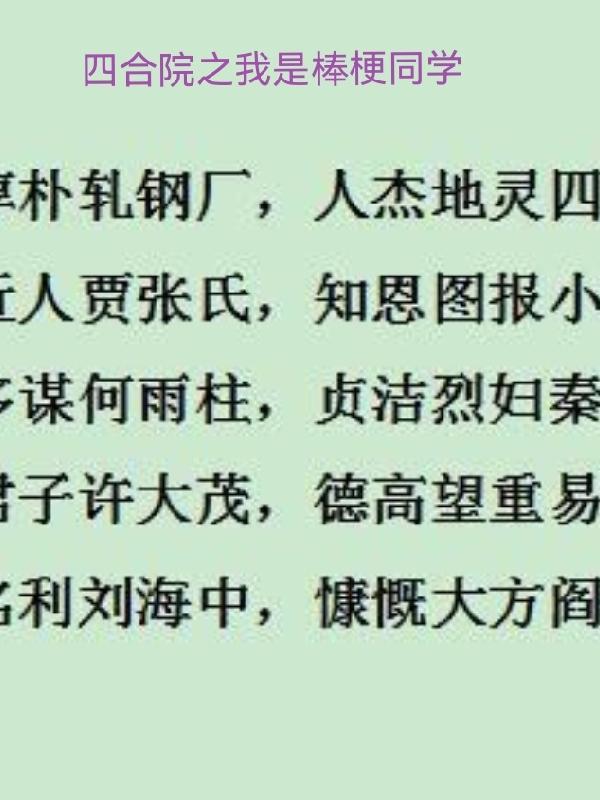69书吧>桃花浅深处的下一句 > 第三章 宇文易(第1页)
第三章 宇文易(第1页)
林少顷看着她满手水泽,微眯起眼,却看不出神情。
那人带着戏谑的口吻说道:“嫂嫂这是怎么了?”
她隐忍慌忙的又到了一杯,递过去。没有回答。又对林少顷说:“妾身身子不适,求大爷让妾身休息片刻。”
余姚含笑春风,道:“林爷刚回来,不知道吧,陶芷妹妹偶感风寒,才大病初愈了,还是叫妹妹好甚歇息吧!”
林少顷端起酒轻酌了一口,随后放回案几,片刻,点了一下头。
陶芷缓缓退下。
不久,剩下的三人又侃侃而谈,一时饮酒作乐。
林莫隐背靠椅子,好似全身无力,眼神飘忽不定看着窗外,又举杯狂饮了一番,蹙眉,道:“这酒不好。”
江启疑惑:“清而不浊,有什么不好的。”
林莫隐摇头,道:“非也,非也,那是江兄甚少沾酒。又怎么会品酒。”
林少顷,说:“你倒是好,必定偷偷藏酒吧!还不快去拿。”
林莫隐依言去了。
陶芷心烦意乱想着天香的种种,心里愈忐忑不安。她温顺安定,可这后矛头回回冲着她来,虽然打了袁璇莹,但林少顷越是沉默不语,越是让人不寒而栗。
而余姚也是个笑面虎,至于她的小叔子林莫隐,一见到就胸腔无比愤闷无处作,越想越头疼欲裂。
已经不知不觉黄昏降临,陶芷面无人色的跑在九曲长廊,朱红十柱上一盏盏清丽梅花灯,晕开微弱余光,洒在青幽幽的石板上,冷冷清清。
那远处白锦无纹香烂漫的梨花,玉村琼葩好似堆着皑皑白雪。黄昏沉沉寂静,浮光霭霭,冷浸了溶溶月。
陶芷犹如断了线的风筝飘然凌落在梨花树下,思绪悠扬,只有这课梨花树才会一种归属感。
她清晰的记得在山上小木屋前也有这样一颗梨花树。人烟罕至的山间,夏季梨枝搓线絮搓棉,搓够寸寸欲断千寻,用来放纸鸢。
春季,在猎户爹爹喋喋不休的担心声中,拿着花篮,一口气爬上树,摘下瓣瓣雪白的梨花,用它做着青酒醉梨花。即便是在大雪铺天盖地的冬季,为了捕捉野兔,在枯槁的梨树,遇见了他——宇文易。
那是寒风凛冽的午后,陶芷拿着用竹枝做的精巧的弓箭,踏着吱呀作响的雪,看见从雪洞中出来一只灰绒绒的兔子,探出头东张西望,过来了半响,才探头探脑的爬出洞,雪地里静谧无声,陶芷弯着腰,府身偷偷摸摸的向前,哪知无意中踩到枯枝,兔子听到动静,一灰溜儿的跑开,陶芷气得跺了跺脚,急忙追了上去,行了约有百余步,那兔子突然在枯萎的梨树下停下,两个乌黑黑的瞳子,乌溜溜的乱转,陶芷不敢上前,拿开弓,突然从灌木丛中出现一个人,可是箭在铉上,不得不,那一箭直冲而去,千钧一一刻,那人身子一侧,箭擦脸而过,留下一条红线,顷刻之间,点点血慢慢溢出。
陶芷惊吓不止,赶忙过出察看他的伤势,指尖轻轻触碰他的脸颊,看了几遍,确定无碍,才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口齿留香。陶芷无意中看见他的眼眸,沉目幽邃,仿佛暗夜苍穹之上的点点繁星,耀眼光泽。
只见那男子轻咳一声,陶芷才回过声来,陶芷收回手,有些不好意思的问:“伤势不大吧。”
那男子说了声“无碍。”
又随手擦了擦已经被寒风吹干了的血迹。
陶芷这才细细打量着那人,衣着褴褛破旧,虽有些瘦弱,但遥遥若高山之独立,面若玉冠。不满道:“你躲在灌木丛中。”
那人微微笑着,如沐春风,让人舒适安逸,道:“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何要躲只不过捡拾一些树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