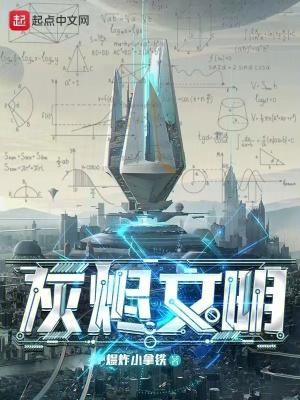69书吧>名人效应法属于 > 第87页(第1页)
第87页(第1页)
邢泱补充一句:“人情不能用到工作中。”
邵峙行就没想过用到工作中,他说:“当然。”
邢泱瞟一眼窗外,天色漆黑,挂钟显示晚上十点。邵峙行顺着他的目光看向窗外,顿时了然,邢泱想赶他走,碍于面子不好说,邵峙行主动说:“我该走了。”
“我送你。”
邢泱立马站起身,拿起外套。
“周云航的事我下周二给你答复。”
邵峙行说。
“好。”
邢泱扶着玄关换鞋,抬头看到邵峙行胳膊上的纱布,视线停住,说:“你这两天洗澡注意点,别感染伤口。”
“哦。”
邵峙行低头摸了下纱布,“不疼,没感觉。”
“该换药了,小区门口有药店,我帮你换。”
邢泱一如既往地周到热情,但保有底线,他不和任何人在同一张床上过夜,即便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用心,几乎让邵峙行以为他们心意相通。
邵峙行有些沮丧,他换好鞋子背起包,跟在邢泱身后,坐进副驾驶,一声不吭地扭头看向车窗外,留给邢泱一个带有情绪的后脑勺。
邢泱系上安全带,疑惑地瞥了邵峙行一眼,这人最近怎么总生气,像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姑娘。
白色普拉多探头探脑地驶出小区大门,邢泱在一家药店门口停下,他小跑几步踏入药店,买一卷纱布和一管药膏,坐回驾驶位抓住邵峙行的手。
邵峙行心头一跳,转头看向邢泱。邢泱低垂眉眼,认真地揭开纱布,小口吹气:“疼吗?”
“还好。”
邵峙行说,他耳尖热烫,指尖酥麻,疼不疼不知道,心尖仿佛挂着一个氢气球,一窜一窜地要起飞。
邢泱将旧纱布装进塑料袋里,把纱布拿出来紧贴着邵峙行的手臂卷两圈,撕掉,剩下的纱布放进邵峙行手心。
“我不想劝你注意安全,你肯定听过无数句注意安全。”
邢泱说,“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不可能不受伤。况且你现在只是娱记,你以后成为一名调查记者,受伤事小,进局子事大。”
邢泱重系上安全带,动汽车,说:“我挺羡慕你,你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邵峙行不懂邢泱有什么可羡慕他的,他理想主义、脾气倔、不会说话。上大学的时候,他的老师曾说过他,你这样的性格容易吃亏。他确实吃了个大亏,拘留三天,丢了工作,灰头土脸的投奔北京,身无分文,省吃俭用交电费都够呛。
就算如此,他仍然倔强,执着地认为要报道真实的东西,要让观众知道事情的全貌。
邵峙行是一个民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群体智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邢泱则全然相反,邢泱是个恶劣的精英主义者,他热衷于玩弄舆论,喜欢将观众遛来遛去收获喜悦。他经常把娱乐圈比作精神病院,一群精神病在台下,一群精神病在台上,傻子演给瞎子看,蠢毙了。
然而邢泱说羡慕邵峙行,像落在池塘边清洗翅膀的鹰隼羡慕吐泡泡的红锦鲤。
邵峙行问:“你是讽刺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