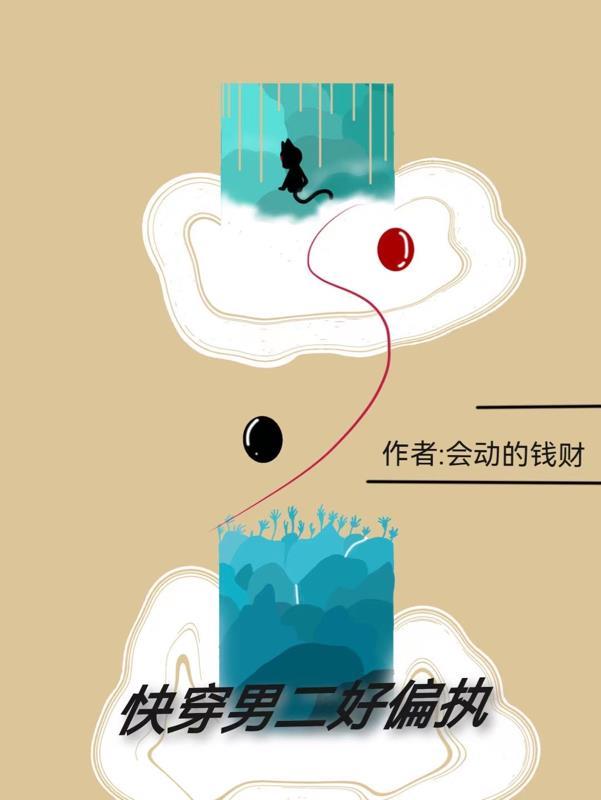69书吧>我的危险性竹马是男男吗 > 第32章 第 32 章(第1页)
第32章 第 32 章(第1页)
卓望道和卓尔婷的声音由远及近,一头各朝一边喊着,一个喊任延,一个喊安问哥哥,十里八乡的鸡都要被喊起来打鸣了。
卓望道喊累了,泄气地说“他俩不会被蛇咬了毒身亡了吧。”
话音刚落,不远处草坡就噔噔迈上来两道人影,一个拉着另一个,被拉着的那个低着头,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
卓尔婷面色古怪,总觉得这俩怎么瞧怎么像偷情。
卓望道“咦”
了一声“你俩没毒身亡啊”
任延懒洋洋的“盼我点儿好。”
夜色下瞧不分明,卓望道左右观察像审问犯人“你俩怎么滚底下去了干什么呢叫半天了都不吭声。”
任延敷衍“学你,抓萤火虫去了。”
敷衍也把戏做足了,他手一伸,手掌摊开,一只原本停于他掌心的萤火虫愣了会儿,懵懵懂懂地浮了起来,似从任延手心点起了一盏小灯、升起了一颗小星。
这盏灯、这颗星都为着安问而来,明灭的萤火间,倏尔点亮他额下明熠的双眼。
卓尔婷口干舌燥,猛地转身自顾自往前走了,似乎突然生了谁的气。
回到福利院,院子里点着钨丝灯,许伯正蹲着身,在大红脸盆里清洗明早要炒的青菜,空气里飘满了肥皂的香味,浴室里热闹得夸张,原来是小朋友们到了洗漱时间。
灯罩下,晕黄灯光引得飞蛾小虫嗡嗡乱飞,卓尔婷眼尖,现任延后背全是草沫和滚出来的泥印子,安问却干净。再笨的侦探也能推断出刚刚两人滚下去时是什么姿势了。卓尔婷泄气地“哼”
了一声,狠狠剜任延一眼。
卓望道“你惹她了”
任延懒散“嗯”
一声,拖腔带调“惹了。”
卓望道“哄哄。”
任延看安问一眼“哄吗”
卓望道不知道这事儿跟安问有什么关系,不等安问回答,任延收回目光,漫不经心地说“哄不了,受着吧。”
福利院的男女洗浴间是分开的,大公浴,一侧是莲蓬头,一侧是贯通的洗手台,两边各能同时容纳六个小孩洗澡或刷牙,没有隔间。整个浴室贴着白色小方砖,虽然看得出陈旧,但维护得十分整洁。
七岁以上的小朋友会自己洗澡刷牙洗脸,太小还无法生活自理的小孩儿,则由护工照料,因此就寝时间前和起床后,都是福利院最人仰马翻的时候。
安问回来一趟,不能光顾着玩儿而不帮忙干活,他拿了吹风机,站在女生宿舍门口,挨个儿帮她们吹头。
穷乡僻壤里,这些小孩大多营养不良,跟过早抽芽的小苗儿似的,细瘦得被风一吹就直晃悠,头软软细细地贴着头皮,实在是个挨个的“黄毛丫头”
。
一听说是安问哥哥给吹,那些原本不洗头的小女孩也洗了,个个包着头巾拿起爱的号码牌。一会儿说“安问哥哥你再帮我吹吹”
,一会儿犯着口吃煞有介事地说“你、你、你比赵伯伯吹得好,他老是刮我头,可疼了”
,那不废话吗,赵叔一双下地干农活的手,新茧摞旧茧的,真丝被他摸一把都得勾丝了。
安问耐心十足,她们说什么,就笑着点点头,指腹轻轻地将她们因为讲话欲爆棚而乱晃的头掰正,拣起一缕长时,动作十分轻柔。
小女生表达谢意的方式十分直接,绞着手指口齿不清地大声说“谢谢安问哥哥,等我长大了我就来跟你结婚”
这一下子捅了新娘子窝,七八张嘴叭叭儿地争先恐后地说“我我我也要嫁给你”
任延半靠着墙,好整以暇地看着安问。他的存在感强得不容忽视,安问却只是低着头,强行假装没看到。
任延不满意他的鸵鸟行径,这满屋子的小情敌他做不到视而不见,心里都把他当白月光,但凡有一个当真的,那长大了以后都不好收场。任延开口,漫不经心地问“安问哥哥打算娶哪个”
安问“”
小姑娘唰的齐齐收声,一水儿地仰头看他,最小的四岁,最大的九岁。
安问收起吹风筒,无奈地打太极“干嘛嫁给哑巴听哥哥的话,长大了一定要找一个能开口说喜欢你的。”
这些小朋友都会手语,都看得懂他的意思,纷纷不服气“就要就要”
安问慢条斯理地卷好线,半垂着脸,低笑着摇了摇头,手语优雅轻盈但笃定“我谁都不能娶,因为我只想娶我自己喜欢的。”
“那你喜欢谁”
忽闪忽闪的乌黑大眼睛仰望着他。
安问愣了一下,抿了抿唇“我谁都不喜欢。”
但这句话不知为何,总觉得有些迟疑,并不是那么坚定,而且怀有心虚的味道,无论如何,他也不敢抬头碰一碰门口那道深沉灼热的视线。
“你骗人哦你耳朵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