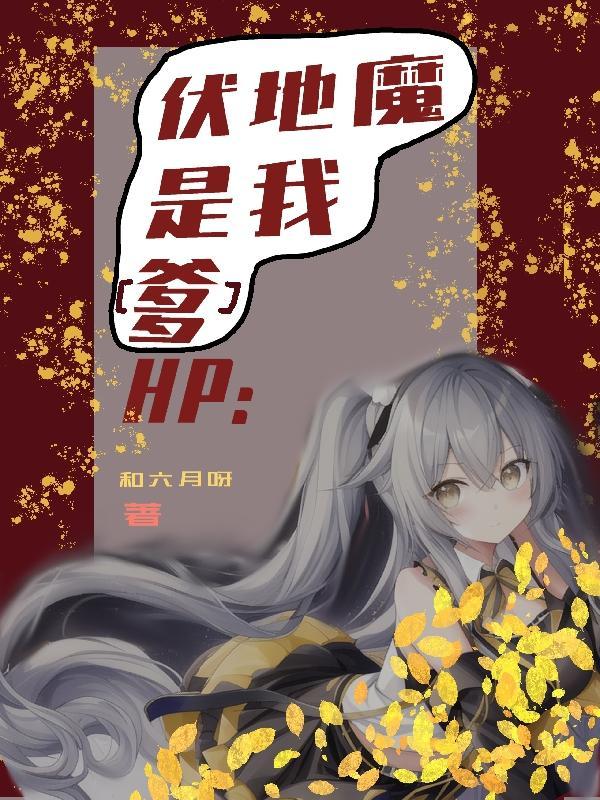69书吧>新安郡王见闻录txt盘搜搜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府兵们簇拥着两人出了院子,正要往外走去,忽见一人披头散发地狂奔出来,见了这群杀气森森的兵丁,又仓皇着扭转身欲夺路而逃——陈果毅正觉得疑惑,王子献定睛一看,心中满含讽刺的冷笑,嘴上却埋怨道:“你们来势汹汹,这种阵仗摆出来,我阿爷还以为你们要将王家当成山匪尽数剿灭呢!”
陈果毅越发惭愧,连忙再度致歉。便听王子献朗声道:“阿爷不必惊慌,只是陈果毅想带着孩儿去一趟长安罢了。许是不几日便会归家,不碍事!”
众目睽睽之下,浑身狼狈不堪的王昌僵硬地回过首,羞恼得恨不得钻进地底下去。他赤着足,又穿得单薄,此时不知该如何反应是好,只得回道:“大郎没事就好!这一路有劳陈果毅照顾他了。”
说罢,也顾不得什么礼仪风度了,转身便疾走回了内院。
陈果毅与一众府兵都有些怔愣,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内院门内。许多人的目光都变得意味深长起来,看向王子献的时候,也不知是同情还是怜惜。王子献只作浑然不知,吩咐庆叟与部曲们继续收拾行装。这时,他留在贤成坊小院的亲信揣着信过来了,同行的还有一位健硕无比的侍卫。
王子献认出了这位侍卫的身份,惊讶道:“阁下替大王送信过来?”
那侍卫拱手行礼:“是!郡王命属下接到王郎君的回信后,便即刻赶回长安。”
王子献拆开信,细细看着,心中的情绪越发复杂难明,似是含着喜悦,又似是带着一二分酸涩之意。家中从未有人替他想过前程之事,然而这位他算计而来的身份尊贵的好友,却替他考虑得这般周全。一片真诚之心,岂能容他继续虚情假意地欺骗?对敌人,自然需要毫不容情地算计谋划;对真心待自己的人,又该如何回报?
没有人教过他,他也并不知晓该如何做,只能依照本心而为了。
小心翼翼地将信件收起来后,王子献微微一笑:“不必回信,我正好要去长安,见到大王之后再分说罢。”
那侍卫满含疑惑地打量了陈果毅一番,陈果毅险些将脸都笑僵了:“这位侍卫若是不嫌弃,便与我们同行如何?”
行李皆准备妥当之后,已是辰时正了。一行数十人立即纵马顺着驿道疾奔长安。到得长安城后,陈果毅领着府兵去皇城递送折子,王子献则随着濮王府侍卫来到延康坊。濮王府素来人丁稀少,李泰与阎氏每日都带着儿子儿媳入宫为秦皇后侍疾,不到日落时分必不会回来。不过,王府长史与典军们都认识这位王郎君,很是热情地将他迎了进去。
不多时,正在立政殿中陪着长宁郡主顽投壶的李徽便接到了消息。他略分了分神,投出去的箭竟是歪歪斜斜地插在了细颈长瓶上头,似坠非坠。长宁郡主已是输了好几箭,见状便转了转眼珠,命宫婢寻出仪仗用的长扇,朝着长瓶用力地打扇子。在几位宫婢的不懈努力下,那支箭终究未能逃过坠落的命运,小郡主立即欢喜地笑了起来。
李徽亦是忍俊不禁:“长宁,这支箭便是掉了出来,你也还是输的。”
“输四箭与输三箭怎么可能一样?”
长宁郡主俏皮地朝着他眨了眨眼,继续踮着脚尖投壶,“说不得阿兄再掉几箭,我就能赶上你呢?”
“好罢,那我们便拭目以待。”
李徽道。他虽有心纵容这位机灵可爱的小堂妹,索性输给她哄她开心,但小家伙生性骄傲,若是刻意相让,反倒是会赌气难受。所以,两人光明正大地一分胜负,便皆大欢喜了。
内间中,秦皇后听着外头的欢笑声,喝完太子妃杜氏手中的药,轻声咳着:“阿徽与悦娘倒是很投契,不过短短一两日,便已经能顽在一处了。”
说着,她拍了拍杜氏与阎氏的手,满面慈爱地道:“兄弟姊妹之间,原便应该如此才是。断不能因些微末之事,便彼此生疏了。你们都是有孝心的好孩子,我心中很清楚。不过,也不能因此就将阿徽与悦娘一直拘在立政殿里。时不时让他们出去走一走也好。”
杜氏与阎氏相视一笑,彼此带着几分难掩的默契:“阿家安心罢。儿们之前还想着,待到上巳节的时候便放他们兄妹跟着兄长们去顽耍呢。如今还是给阿家侍疾要紧,有他们在身边,也能给阿家凑一凑趣,教阿家心情愉悦一些。他们也做不得什么,能够逗阿家开心,说不得倒是沾了不少阿家的福气呢。”
立政殿中依旧是和乐融融,两仪殿内却已是风雨欲来。
圣人拿起商州新递上来的折子,狠狠地砸在地上,怒斥道:“给朕好好地查个清楚明白!!到底是哪些人在背后折腾!竟然敢派死士刺杀朕的儿子!!他们这是想做什么?!想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想让朕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是谋逆!谋逆!!”
他暴跳如雷,殿内的摆设几乎都砸了个干净,几位重臣跪倒在地上,一时间都不吭声。当今圣人的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不过,在事关儿女们的时候,便总会有些执拗。他们只能等着他勉强收回理智,再缓缓谏言,他才能听得进去。
“三司会审!”
在两仪殿中团团转了好几圈,将各种摆设都踹翻了之后,圣人猛然回过首,一字一句道,“着令太子、越王……嗣濮王监审!三郎此刻心里一定难受得很,便无须再让此事折腾他了。”
众臣均松了口气:嗣濮王监审当然比濮王监审更好!濮王若是借着这个机会再度回到朝堂中掌握实权,一定会为日后埋下隐患!看来,圣人虽是怒冲九霄,但到底还未失去理智。他们也不必悄悄让人去知会秦皇后,劳累重病中的皇后殿下进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