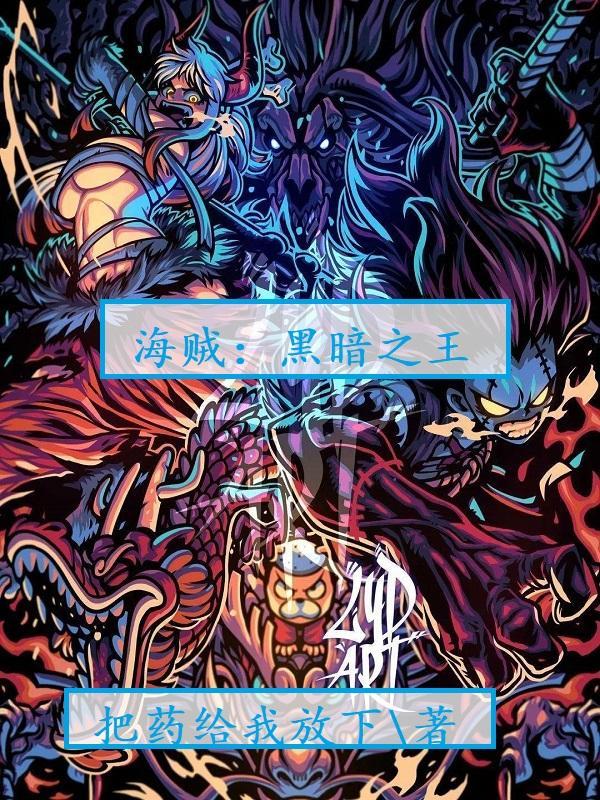69书吧>夫郎家的温润书生txt > 第21章(第3页)
第21章(第3页)
小满崽依着谢见君的话,给谢三和芸娘磕了个头。
这是他没有爹娘的第一个年,哪怕从前芸娘待他算不得好,谢三也不曾像阿兄那般宠着他,带他飞高高,但他到底还是个五岁的孩子。正是在娘亲怀里撒娇的年纪,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小小一只,跪伏在地上,懵懵懂懂地磕头,谢见君红了眼圈,心头涌上来阵阵酸涩,他斟满三杯酒。
前两杯给谢三和芸娘,最后一杯酒,祭奠的是被他占了身体的原主。
他将前两杯酒依次撒在坟茔前,而后双手合捏杯盏,冲着他们来时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将酒泼洒在地上。
“放心走吧,我既是占了你的身体,便会照顾好满崽,直至他将来长大成人。”
风吹过树林间哗哗作响,卷动着落叶在半空中飘转两圈,悠悠然落在他二人身旁,似是在呼应着谢见君。
“阿兄,起风了。”
满崽扬起半个身子,伸手接住枯黄的落叶。
“是啊,起风了,咱们该回了。”
,谢见君将他扶起来,把祭拜的贡品重新收回竹篮里。
他拿出铁锹,铲起一黄土,缓缓地将新土铺洒在谢三的坟茔上,用铁锹的背面把新土轻轻敲严实。因着芸娘是新坟,下葬不满三年,故而用不着添土。
那些烧完的黄纸,他用水浇灭火苗,不放心又铲了几处雪,盖在纸灰上,只等着不冒烟了,才牵着满崽的手,二人慢悠悠地往山下去。
下一次再来,便是清明了。
年三十,雪过初霁。
不同于往常贪懒,今个儿村里人早早就忙活起来。
谢见君推开屋门,长长地抻了个懒腰,难得给自己放了个假,今个儿没温书,他将水缸里的浮冰敲碎,舀出大半盆水来,倒进锅中烧热,只等着云胡和满崽早起盥洗。
昨日云胡和满崽堆的小雪人孤零零地立在院子里,不晓得夜里哪里来的野猫,啃去了小雪人充作鼻头的半截子胡萝卜,没了鼻头的小雪人瞧着有些滑稽。
谢见君犹自笑了笑,折下一小节树杈,充替了那半截胡萝卜,这般看起来,才有些顺眼。
云胡姗姗来迟,穿戴好衣衫从卧房里出来时,灶房里的炉火烧得正旺盛。
“地上滑,慢些走。”
谢见君刚刚把院子里的落雪推到一处,回叮嘱云湖小心看着点脚下的路。
云胡点点头,下石阶的步子果真慢了下来。
“今、今早喝米粥、如何?”
他站在灶房前,冲谢见君扬声道。
“行,简单吃点,留出肚子来,夜里咱们吃栗子鸡。”
谢见君摸去一把额头上的细汗,笑着道。
昨个儿他俩便商量好了,今日的年夜菜杀只鸡来吃,加之先前从后山摘回来的鲜甜栗子还余了些,一道儿炖上满满一锅,好开开荤。
往年的年夜饭勉勉强强只能沾点荤腥,如今却是可以吃一整只鸡,过惯了苦日子的云胡和小满崽也不免对年夜饭生出了几分期待。
吃过早饭,家里没什么活,索性谢见君就让满崽跟着小山去村里讨喜,免得一会儿杀鸡放血再吓着小家伙。
云胡正在灶房里忙活着准备守岁的饺子馅儿,谢见君提着刀进来,面露难色,窘得手脚都不知如何安放,
“云、云胡,你会杀鸡吗?”
,他在院子里好不容易抓了只老母鸡,左右犹豫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这才来灶房里问问云胡。
年轻的教授先生博学多识,知文达理,唯独不曾进修过杀鸡这门行当,此时臊得脸通红,神色都带上了不自然。
“我、我试试吧。”
,云胡将菜刀往案板一搁,围裙上抹干净手,同谢见君一前一后出了灶房。
院子里,老母鸡被捆住双脚,倒挂在墙壁上,扑腾得到处都是鸡毛。
云胡从谢见君手里接过刀,颤颤地往墙边走,一脸的视死如归。他哪里是杀过鸡的,从前家里吃鸡,娘亲都背着他,生怕他多惦记一眼。
谢见君瞧着云胡步伐虚浮,实在不像是个熟手,他正要开口说算了,要不还是自己试试,话刚起了个头,就见云胡紧闭着眼,手中的刀高高扬起,一刀砍在了墙上。
鸡毫无伤,刀卷了刃。
倒挂的老母鸡折腾得愈欢腾,好似在庆祝自己又逃过一劫,只余着二人面面相觑。
云胡提着卷了刃的刀,不知所措地看向谢见君,那局促的神色比哭了还要难看。
“没事。”
谢见君干巴巴地安慰道。刀不刀的无所谓,只是这鸡,还不知道今日能不能吃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