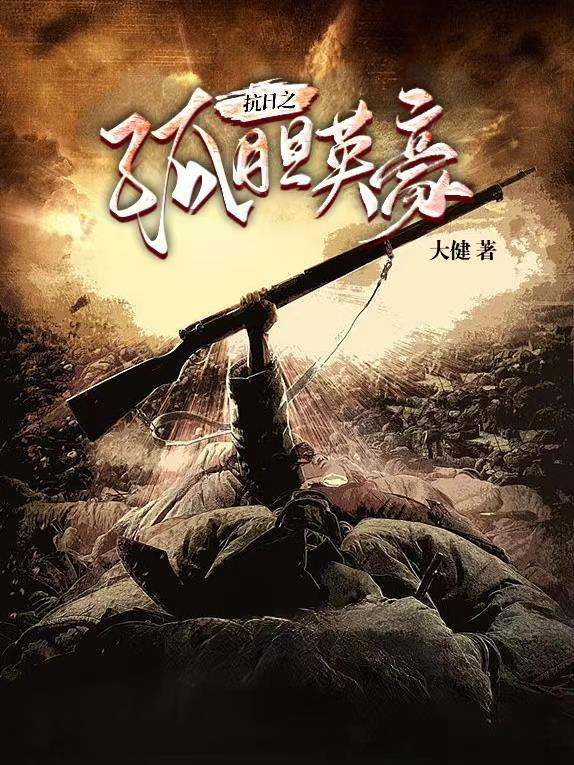69书吧>褪粉梅梢青苔上讲什么 > 第96章(第2页)
第96章(第2页)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丁副官冷冷说道,“黄先生不为你自己,也得替你母亲下半生能否安度晚年考虑考虑……”
黄启伦的嘴唇都紫了,半晌之后,他才一咬牙,在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然后将笔远远地一抛,捧住脸,颓废而痛苦地蹲了下来,肩头耸动起来。
龚梦舒面色苍白,对黄母低声说道:“以后请您多照顾启伦吧。”
便转身随着丁副官离开,她甚至没有进屋去取走自己的东西。
“梦舒,梦舒——”
龚梦舒走出了很远,也能听见黄启伦还在嘶哑而脆弱地在背后喊着她的名字。她的鼻子一酸,眼泪终于扑簌簌地滚落而下,滴湿了衣襟。丁副官也叹息一声,小心翼翼地护送着龚梦舒上了车。
丁副官发动车子,准备将车驶往程瑞凯的公馆梅园。龚梦舒却阻止住了他:“丁副官,请送我回龚家。”
“可是龚小姐,司令有令……”
丁副官为难地看向龚梦舒。
龚梦舒面无表情道:“你据实跟他说即可。他若是还不依,你让他到我家来把我给枪毙了!他不是向来都喜欢干这种威逼利诱的龌龊事么?”
说着转头望向车窗外,不肯再说话。
丁副官见龚梦舒面色阴沉,大有玉石俱焚的豁出去架势,便也不敢多说,只得将车子调转方向,开往龚家而去。
车行半道,龚梦舒让丁副官将车子先开到教会医院,想去看看父亲和母亲。丁副官不敢违抗,听从了龚梦舒的意见,将车子开进了医院里。
龚梦舒让丁副官在教会医院外面等候,自己缓缓地走进了医院。结束了一场并不适合的婚姻,她的内心却没有一种解脱的释然,而是充满了浓重的压抑感。一切仿佛是场梦,可是她却找不到让梦清醒的有效方法。
她在病房门口站立了片刻,才轻轻推门进去,但进去之后却发觉原本父亲躺的病床却空空如也,病床的一边也不见母亲的身影。龚梦舒在瞬间便白了脸,她愣在那里一会儿,随后犹如发了狂一般冲出病房去找大夫。
“大夫,我的父亲呢?他,他怎么了?难道他……?”
龚梦舒抓住了一位医生,颤声问道,觉得自己的双腿发软,差点就跪了下来。
“哦,小姐是说那张病床上的病人么?”
医生看了看龚梦舒所指的方向问道。
“是的,病人怎么了?您能告诉我么?”
龚梦舒一眨不眨地盯着医生问道。
医生见龚梦舒如此紧张,便笑了笑安慰她道:“病人今日转到单人特护病房去了——”
“啊?”
龚梦舒见父亲并没有出意外,悬着的心这才落回了原处,但随后她便狐疑地问道:“是谁让我爹转病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