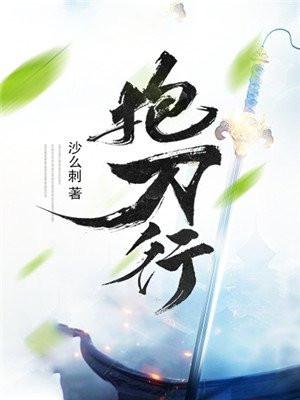69书吧>民国人物传记有哪些 > 第6页(第2页)
第6页(第2页)
这位以传教士自居的留学生,又是一位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批判精神、改革运动、调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个个关键词,在在反映出他的意愿——他想要改变祖国的现状,为中国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梦想。
一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
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
。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8]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
的胡适来说,他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
,他也的确做到了。
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文明,后来他在《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
(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胡适希望“折衷旧,贯通东西”
,[9]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
,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详后)。[1o]
这样的大目标,到他撒手仙去之时,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是很成功的。
不过,胡适一向提倡“尝试”
,也常以“但开风气不为师”
自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功,已足名留青史;其实际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以他爱引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来说,自从胡适回到中国,这“不同”
是明显而实在的。
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
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
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
了。[11]
而胡适遗存下来的更多贡献,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的贡献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
[12]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13]在“苏文熟,吃羊肉”
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