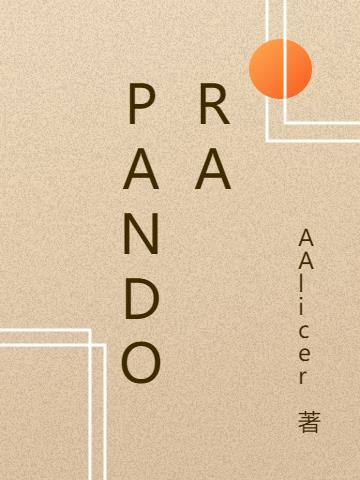69书吧>春风不相识太监 > 初识隔纱布玩指J到S太监的首次颅内(第1页)
初识隔纱布玩指J到S太监的首次颅内(第1页)
自打余阳夏亲口答应了要做阴容的孪宠之后,阴容连着三天都没怎么回自己府里。一方面是因为前段时间余阳夏昏迷的时候,他推了一切公务去照顾对方,一些重大事务推了再推,再不做出决策恐怕下面的秉笔太监都要一头撞死在他跟前了;另一方面,阴容的心里很乱,他没想到余阳夏会同意,当时说出口的时候他只觉得有种自毁般的快感,认定了这话一出口,两个人的缘分就算是亲手被自己毁干净了……但是余阳夏再一次接住了他。
阴容心理阴暗,习惯了什么事都往最坏了想,于是觉得余阳夏只不过是为了求他庇护、受他胁迫而已,但又没办法骗自己,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余阳夏答应自己的时候,是笑着的,这又怎么能不让他心生妄想呢?
希望与绝望的来回拉扯,让阴容不知道如何面对余阳夏。不过余阳夏身体还在恢复,一时间没办法履行那孪宠的指责,加上最近确实公务繁忙,索性就借着这个理由避开余阳夏,也是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只不过余阳夏到底是久经沙场练出来的强健体魄,从昏迷中清醒后恢复得很快,如今已经能下地行走,刚刚还托屋里的内侍过来问阴容在哪里,怎么还不回来。阴容心知再无法拖延了,正巧拜托晋王帮忙采买的物件也到得七七八八,干脆捧起装满了稀奇古怪淫物的木盒,往卧房走去。
……
余阳夏这几天也是颇为煎熬。
他不想显得自己太急色,真像个孪宠似的勾着主子争宠,但是他迫切地想要确认阴容对自己是否有欲望……又或者,他可以奢望阴容对自己有感情。只是余阳夏了解阴容,他此刻必然是摇摆不定,怀疑自己是委曲求全,不肯相信自己的感情。这是他黑暗的过去给他留下的,余阳夏知道一时间治不了他这个敏感多疑、凡事往最坏想的性子,但是情迷意乱时的肢体动作骗不了人,余阳夏只想从中窥探几分那人的心思。
但是,怎么才能把一个太监勾得意乱情迷呢……?一贯被评价为不解风情的余将军有些苦恼地想。
这时阴容推门而入,打断了余阳夏的思索。
“咱家一向是不喜欢强人所难的,特特给余将军留了几日思考,余将军可想清楚了,是你自愿当孪宠求咱家庇护的,咱们各取所需罢了……别到头来又怪咱家折辱你了,咱家可承不起镇北将军府的怒火。”
阴容皮笑肉不笑,眼神阴测测地盯着坐在床上的余阳夏。
余阳夏站起来直视阴容的眼睛:“我先前就说了,是自愿的。”
他说话总是这样直不愣登的不会拐弯,但却格外的沉稳笃定,叫人听了不自觉地心里信服。
眯起眼睛定定地与余阳夏对视,阴容有意地用眼神施压,照理说是挺吓人的,曾经有被抓到东厂审讯的人只是被阴容这么看了一时半刻,便吓得什么都招了。但余阳夏毫不畏惧,一双清澈坚毅的眼将他的视线照单全收,看不出一点心虚和动摇。二人就这么四目相对了一会,阴容先移开视线,嗤笑一声道:“既说明白了,那就开始吧。”
“放心,咱家顾及着余将军身子尚未大好,不会玩得太过火……余将军只要乖乖听咱家的,保证让你爽得欲仙欲死。”
刚刚还分毫不让地与阴容对视的人,只是听了这句根本称不上荤话的荤话,便眼神躲闪了起来,颧骨处掠过一抹薄红:“那……我该怎么做?我不会。”
就这一句话,直接把阴容心里的火点着了,险些压不住体内的兴奋。他的小将军太会勾人了,还说什么不会?
“看来余将军这方面学术不精……不过咱家心善,自会好好调教你的。”
阴容眼神晦暗不明,舔了舔唇道,“现在先坐到床上去,把衣服脱了。”
余阳夏想到要在心上人面前袒露身体,既羞涩又有些隐秘的期待,没有太多犹豫就伸手解开了中衣的带子,露出被纱布层层包裹的胸膛。余阳夏原本身材极好的,身上都是漂亮又充满力量感的肌肉,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柔韧的脂肪,可如今鬼门关前走了一回,却是轻减了许多,显得有些瘦削了。他脱了中衣,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身材,自己也觉得不如从前,有点担心吸引不了阴容,颇为不自信地去看阴容的脸色。只见对方一张天仙似的脸染了欲色,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身体,凤眸中的火险些一路烧出来,余阳夏就知自己对他来讲还是有魅力的,心中放松,干脆松手让缎子做的中衣流水一样落到地上。
阴容定定看着面前那只着了亵裤的躯体,麦色的肌肤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疤痕,胸口处缠着惨白的纱布,隐隐渗出血迹。这种残缺破碎的样子更加勾人,阴容只感觉身体中有一股陌生的火在乱窜,无处发泄,想要狠狠地蹂躏这具身体,摸遍浑身上下每一个角落,掌控他的欲望,让这伤痕累累却又精瘦而充满力量感的、战神般的躯体臣服于自己。
阴容再也难以克制,伸手将余阳夏推倒至床头,战场上屹立不倒的将军顺从地躺下,让阴容跨坐在自己腿上。
宛若柔荑的白皙手指抚上余阳夏线条硬朗的侧脸,引得他眼神颤抖,忍不住将脸往那手心里靠,阴容却轻笑一声,手指向下移动避开了,指尖贴着皮肉,似触非触、若即若离,一路向下划过不断吞咽的喉结,到锁骨,再到胸口那纱布上。
“这纱布倒是碍眼得很,咱家都没办法好好玩将军的奶子……”
说着阴容准确地将指尖按到了乳头的位置,隔着粗糙的纱布轻轻地绕圈。余阳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看似没用的器官也能给人带来快感,还要加上那纱布的摩擦,叫他体会到一种酥麻的爽感,忍不住粗喘起来。分明阴容的手指只是在乳晕打转,都没有直接刺激到乳头,但他却被玩弄得乳头挺起,将纱布顶出一个小包。
“将军的奶子好生淫荡,都没有碰到就已经立起来了。”
阴容发现用这种淫词艳语刺激余阳夏特别有效,每每听到直白淫秽的话,余阳夏的脸色就变红一分,喘息也更加明显,一副十分情动的样子。这样的余阳夏真的太过色情,阴容有些失去耐心,只想狠狠地玩弄对方,便用上两只手齐齐按上余阳夏两边乳头,隔着纱布快速拨弄立起来的乳尖,时不时用指甲刮搔。
快感瞬间增幅,余阳夏受不住地挺起胸口叫出声来:“啊……太快、别……”
与此同时,从刚刚被阴容抚摸脸颊开始就有些勃起的下身彻底硬了起来,直挺挺地抵着阴容的后臀。余阳夏无意识地挺起劲腰追逐快感,一下下地隔着亵裤蹭阴容,分明阴容身上穿戴整齐,只是隔着那么多层布料摩擦,却让未经人事的余阳夏爽得有点头脑发懵,阴茎硬得要把薄薄的亵裤顶穿,甚至帐篷的顶端都有了一丝湿意。
感受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抵着自己的臀缝一下一下地顶撞,阴容其实因为对方动情的反应而非常愉悦,但面上故意一沉,反手抓住那根精神奕奕的东西,诘问到:“余将军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看咱家是个阉人,故意拿这物什膈应咱家不成?”
命根子被紧紧攥在手里,挤压带来疼痛的同时也有几分莫名的快感,阴茎反倒搏动得更起劲了,亵裤顶端的水痕也逐渐扩大。余阳夏气息不稳,但方才还一片情欲迷蒙的眸子多了一丝清明:“不是的……我怎会…呃,轻点……”
阴容手上力道愈发大,余阳夏被攥疼了,不由伸手去握阴容的手腕。
阴容却不管他辩白,厉声呵道:“手放下!玩你自己的奶子去!”
余阳夏看阴容沉了脸色,怕他真的不开心了,顺从地把双手放到胸前,却为难地不知如何是好。阴容冷眼看着对方青涩稚嫩的样子,口气冷淡地指挥起来:“拇指中指捏着乳头,用食指摸你的骚奶子……快一点,用力一点。”
自己玩弄奶子却和阴容动手有不一样的感觉,快感没那么尖锐强烈,但羞耻心却涌了上来,身体都好像更加敏感了。余阳夏微张着嘴喘息,时不时泻出几声压抑的呻吟。
阴容看他进入了状态,满意地俯下身去进行下一步。他先是扒掉余阳夏身上最后一件亵裤,那根硬挺的阴茎便蓦地跳了出来,形状漂亮挺拔,个头也出众,是个没怎么使用过的淡粉棕色,覆盖着狰狞的青筋,唯有龟头因为快感涨得通红,小孔不断溢出透明的汁液,随着茎身的抽动被甩落。
先前倒是听说过有些太监被去势后,反而会对男人的阳具产生狂热的崇拜,阴容此前并不太理解,但此刻看着眼前这根堪称完美的尤物,却好似有点懂了。忍着触摸虐玩的念头,阴容略过勃勃跳动、欲求不满的性器,直奔臀瓣间那处隐秘的穴口。
余阳夏正沉浸于乳首的快感中,突然感到冰凉的手指触碰到了敏感的会阴,紧接着就摸上了那个小洞。
纵使余阳夏肖想阴容多年,从来没想过阴容会委身他人作为被进入的一方,自然也做了心理准备,但任谁,热热闹闹地吃喝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只有余阳夏的目光默默地追随着太监的队伍,看着末尾那人踉跄地追着前面,背影消瘦得好像凛冽的北风能把他吹散了似的。
即使受辱如此,那人都始终没有看过自己一眼。
是不记得自己了吗?
十岁的余阳夏觉得有些难过,但随着他慢慢长大,却觉得这样也好。
别人或许看不出,但余阳夏见过御花园里阴容被他发现时的眼神,和他流着血搬那盆珊瑚时如出一辙——阴容动了杀心。
自从那次生辰宴之后,余阳夏央着父亲,想把阴容调到自己府上,好让他不要受这么多委屈。但那次父亲没有同意,而是抚摸着他的脑袋,神色难得地有些无奈和复杂:“那孩子……身份太过敏感,当年那案子是皇帝亲自下的判决,任何人同他扯上关系,就相当于直接驳皇上的面子。”
“虽然可怜,但他现在只能靠自己。其他人的帮助只会为他招致猜忌。”
“你若想帮他……就悄悄地帮吧。”
因着这句话,余阳夏在背地里偷偷帮了阴容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