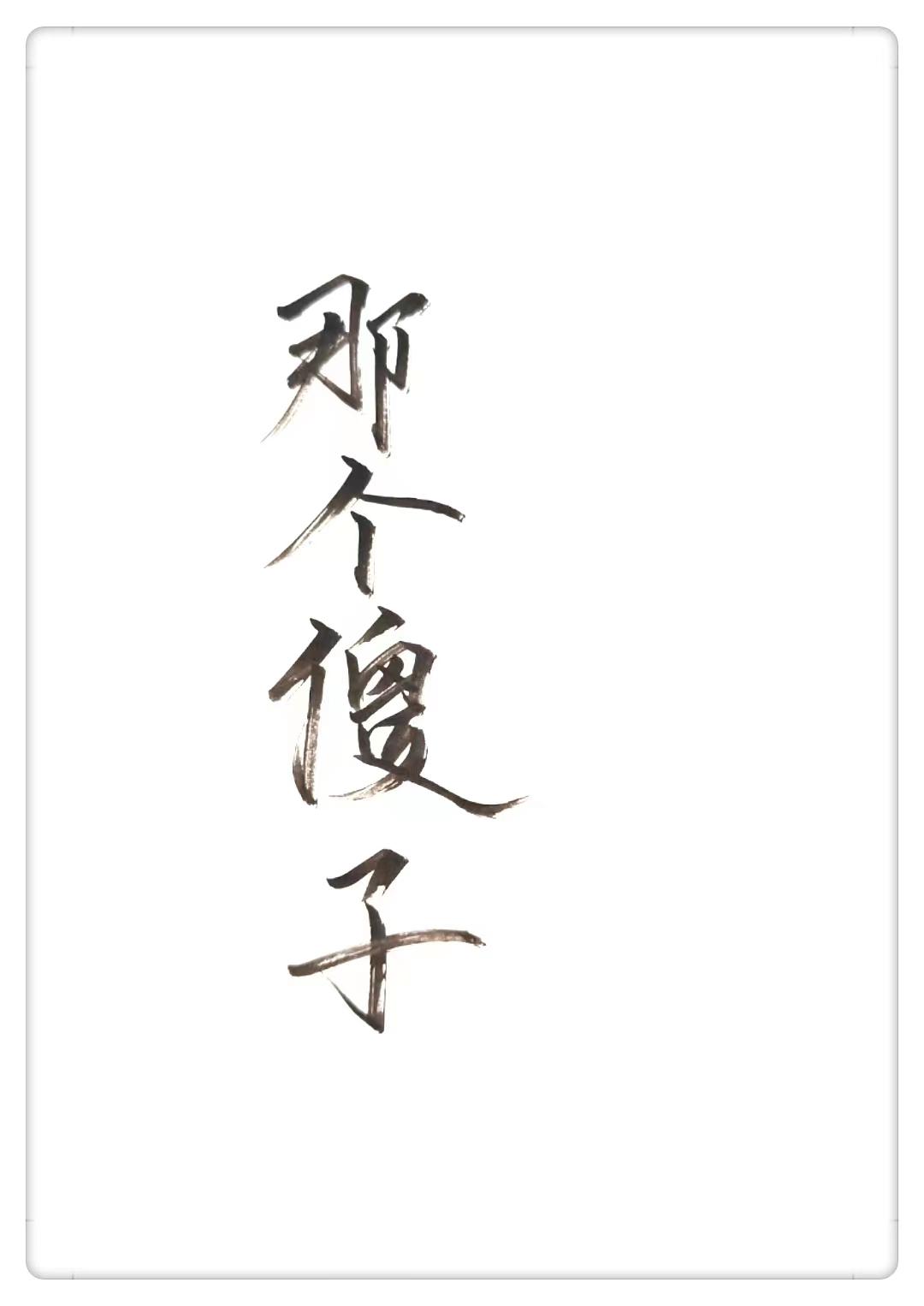69书吧>重生后太子妃咸鱼了免费 > 第13节(第3页)
第13节(第3页)
张皇后道:“老夫人过谦了。七娘也在家中待不了多少时日了,我怎生忍心抢人。”
女官以袖掩口,吃吃一笑:“奴婢倒有个两全之策……”
却不往下说。
张皇后笑着剜她一眼:“好个刁滑妇人,偏你话多,在客人面前搬弄口舌,是生怕我不治你的罪?”
那女官一脸有恃无恐,笑道:“奴婢死罪,不该妄自揣测皇后娘娘心意。”
张皇后笑骂:“果真死罪。”
两人一递一说,就差把话挑明了。
沈宜秋偷觑祖母脸色,只见她若有所思,微露沉吟之色,不由心焦。
祖母的心思她一清二楚,如今与宁家还未过定,尚有转圜的余地,可是背信食言究竟于名声有损,沈老夫人一向以门阀自矜,多半是在举棋不定。
她不能将自己的后半生悬在祖母的一念之间。
沈宜秋心如电转,便即低下头来,双手拉扯绞动着腰间的丝绦,娇羞之色溢于言表。
宫中女子目光何其敏锐,见她这模样,心下便有了计较。
张皇后沉吟片刻,对沈老夫人道:“七娘如此品貌,贵府的门槛怕不是已经被踏平了,不知哪家的公子有这般福气。”
沈宜秋将头埋得更低,沈老夫人看在眼里,心头火起,但却毫无办法。
皇后既已看出端倪,刻意隐瞒便成了欺君。
且宁沈两家议亲之事虽未传扬出去,到底不是什么秘密,皇后既起了疑心,着人一打听就能知道。
她只得道:“回禀皇后娘娘,孙女许了宁家二房十一公子,现下还未过定。”
张皇后虽已猜到,仍不免遗憾,对女官摇头叹道:“就知晚了一步。”
又将沈宜秋叫到跟前,拉着她看了又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张皇后与沈家祖孙说了会儿话,又留他们在宫中用了午膳,赐下若干赏赐不提。
从宫中辞出,沈家祖孙同坐一乘马车回府。
刚一上车,沈老夫人便沉下脸来,目光如刀地盯着孙女,仿佛要在她花般娇艳的脸庞上盯出两个窟窿:“我悉心教导你十年,你学的便是自行其是,悖逆长辈?”
沈宜秋泰然自若地迎着祖母的目光:“孙女不知何错之有,望祖母明示。”
沈老夫人不曾料到她这么大胆,一时无言以对。
她为何勃然大怒,两人都心知肚明,但理由不能摆到明面上说。
世家的体面就在这一层捅不穿、扎不烂、水火不侵的遮羞布上。
半晌,沈老夫人长长叹息了一声:“你且好自为之。”
说罢靠在车厢木壁上,阖上双目,再也不发一言。
若是换了以前,沈宜秋见祖母不豫,必定十分自责,哪怕委屈自己一辈子也要换祖母展颜,可上辈子一二再再而三,让她将沈家人的面目看得清清楚楚,如今她心里只是波澜不惊。
沈老夫人也知无力回天,这回干脆懒得罚她。
text-align:center;"
>
read_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