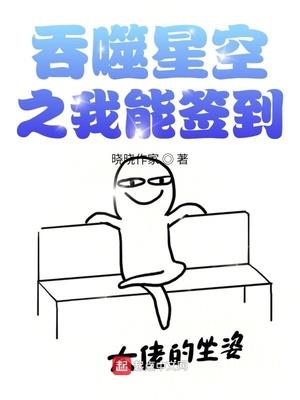69书吧>乾坤已定近义词 > 第5章 大失所望1(第3页)
第5章 大失所望1(第3页)
赵鞅解释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你的确与此事无关,怕什么查?”
“我是否与此事无关,不必向你交待。”
说完,智跞冷哼一声。
“你没有否认,此事就跟你脱不了干系。”
赵鞅得出结论。
“有关也轮不到你来定罪。”
智跞睥睨赵鞅,神情冷傲。
“这么说,你是收了祁胜或是邬臧的好处,所以一心一意要置祁盈于死地了?”
赵鞅心冷口冷,说道:“祁氏一门,效忠公室,正直无偏,你为了一己之私竟要将他们满门断送,于心何忍?”
“他们有错在先,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智跞轻描淡写道。
“两家满门上百人的性命,在你眼中竟如此轻贱?”
赵鞅一边说一边摇头,语气沉痛,“你我相识三十载,今日才知——你竟是个心肠歹毒的贪婪小人。”
赵鞅的话说得很重,智跞被刺痛了,整个人像被火点燃了似的,他跳起来,高声吼道:“不要含血喷人!祁胜是有拜托我,请我替他向祁盈求情。我还未及开口,祁盈已将他拿下。无奈,我只得央求君主扣押祁盈,以示处罚。谁知——”
“祁氏家仆为主子不平,把祁胜、邬臧杀死,羊舌食我又借机生事。”
“于是你就推波助澜,借机将两家清除干净,以此向君主邀功。”
赵鞅指着智跞,横眉竖目。
“事情展到此境地,已经大大出我的预期。”
智跞极力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杀死家臣,犯上作乱,这两项罪名都是杀头重罪,与我何干?”
“如果不是拿了祁胜的好处,你何必央求君主扣押祁盈?如果没有扣押祁盈,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就不会生。所以,这件事情的罪魁祸——就是你!”
赵鞅眼睛喷火,青筋暴跳,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你是怎么也要把罪名往我身上推就是了,我就是周身嘴也说不清。”
赵鞅道破真相,智跞有些恼羞成怒,无奈理屈,只得勉强支撑,做最后的挣扎。
“如果你不收祁胜的财物,我就是一身的嘴也不可能把白说成黑。”
赵鞅得理不饶人,“我俩时常挞伐士鞅,说他贪财短视,财迷心窍,对他嗤之以鼻。何时你竟变得跟他一样,为了财币颠倒是非,戕害人命?”
“我何时颠倒是非了?”
智跞的火气又上来了,扯着嗓子说道:“家臣所犯的错,罪不至死,可轻可重,是祁盈仗着主子的威风借机生事,又不报与君主,他是罪有应得。”
“报与不报,无关生死,更不能牵连家小。你是强辞夺理,为的是减轻自己的罪孽。”
赵鞅不接受智跞的歪理,不给智跞逃避责任的借口。
“如果祁盈不扣押家臣,就什么事都没有,一切都不会生。”
智跞态度轻蔑的说道:“无论如何,罪不在我。”
“如果祁胜、邬臧没有做下违背人伦的荒唐事,祁盈又怎会抓人?如果祁胜没有厚礼送给你,你又怎会不遗余力的替他开托?如果祁盈不被逮捕,祁氏家仆又怎会替主子不平,将二人杀死解恨?羊舌食我又怎会无缘无故向国君讨要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