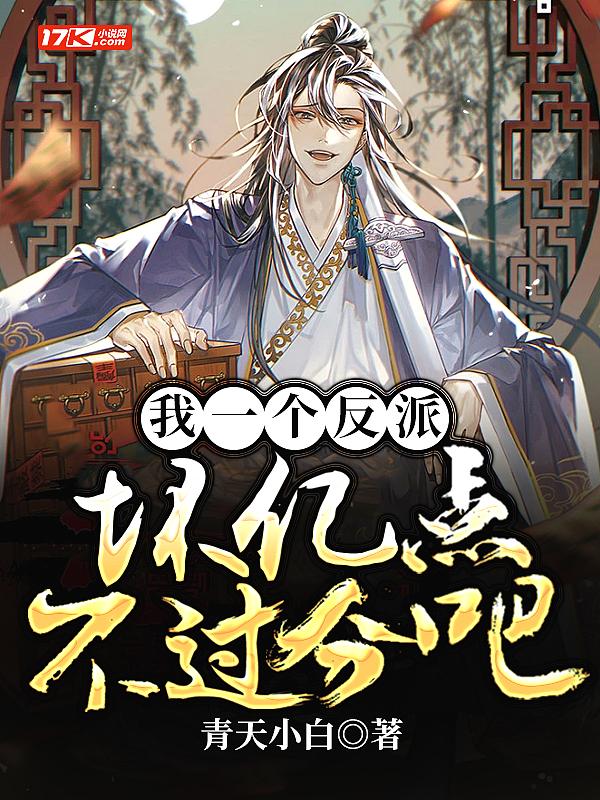69书吧>贵妃娘娘千秋by年年雪在 > 撑腰(第2页)
撑腰(第2页)
背后,也是芙蓉雪肉垒起的汹涌波涛,像是一怀流化的春水,酥酥腻腻,磨人心窍。
还有指掌间游走的痒热。
萧无谏心神为之一荡。
语气却不见什么波澜,稳声对隋安道:“那宫人叫莺时?押入内狱,不必再审。”
这旨令简明扼要。
隋安步子堪堪迈定,忙应道:“是。”
人还没站稳,又匆促地退出去了。
隋安本做好了被问话的打算,没想到陛下什么也没多问,像是早已有了考量。
内间。
孟绪很快领悟到了帝王的用意。
和内狱的刑讯手段相比,柔妃今日让人动用的刑罚,恐怕都算的上和风细雨。
若真进了内狱审问起来,莺时自然捱不住。
可不必再审,那就是没有这个审问的必要了。
因为倘若莺时没说谎,那么不管是有人故意让她看到伪造的景象,还是她自将小小红疹误看作了溃伤,她都是选择了将这件事捅出去,当成自个儿的踏板。
此等卖主求荣的仆下,断不必留。
可若莺时并没有看到,而是有人教她那么说,那教她这么说的人,除了她的主子,也就是此事唯一的利好者,不作他想。
为虎作伥的罪婢,亦不必留。
所以莺时怎么样都要下这个狱。
而比起莺时的口供,帝王显然更愿意,也更相信,从别的地方所得知的答案。
比如,换个人审,他亲自来审。
“卿卿没什么要与朕说的吗?”
保持这个姿势,萧无谏看不到身后缠附的女子刻下是如何千娇百媚的情状。
只听见她清清冷冷地道:“妾没派人去请陛下,陛下信么?”
与她靠上来时,周身那宛如烟流水泄的香息不同,她的嗓音一贯清冽。
而此刻,孟绪正想到,或许他不由分说将人收押,也是想看看她会不会为莺时求情?倘或求情了,不就说明莺时与她是朋党共犯之流?
于是,热霭烘人的被底,那只冰清玉凉的纤手忽而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撤了出去。
萧无谏捉之不及,隐隐有些不满。
口中却不疑:“看来,是卿卿的人唯恐你遭人欺负,擅作主张。”
可还没等他向后侧眼,去寻找失落了的那把嫩软的水葱。它竟又自己重新追缠了上来,攀援在他的襟前——
胆大妄为的女子,竟以一手自后绕到了他的衣襟上,贴在最靠近心腔之处,一点点溯流而上,缠绵摸索,占尽先势。
做着昏沉的事,却说着最清晰、最清醒的话:“陛下既信不是妾让人请的您,那么妾单单教唆莺时这丫头,去空自诓骗陈妃娘娘与柔妃娘娘一遭,又有什么好处?总不能是想让二位娘娘白白心疼妾一回?还是说,是想引诱让她们兴师动众地来揭破妾的谎言。”
迄今为止,浮出水面上的事实中,她既得的所有利益,无不与他今日的亲至有关。
一为博他关心探问,二为让陈妃与柔妃在他面前闹了个乌龙,打了她们的脸面。其余,还有什么?
那么,只要不是她派的人去请他,一切也就都不成立了。
萧无谏轻轻呵笑:“有理。”
他忽将手覆在了衣前的那只手上,然后也同样毫无预兆地,擒锁住了那一寸细腕,有些不解风情地将它微微带离。
在孟绪正疑惑他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猝然转身,整个人霸道地向她欺上。
身还未贴至,霜松风柏一般的气息先将人侵裹。
孟绪不得已向后仰倒。一只手被他举过头顶,压在松软的豆枕上,失去了一半防备之力。
“陛下?”
她用还能活动的那只手抵住他压过来的胸膛。
可是一点也抵不住。女子与男子力量究竟悬殊,他轻而易举,就把她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卿卿可知,何为后来居上?如此屡施先手,撩拨于朕,就不怕朕,”
萧无谏眼神浊重,顿了顿道,“不再顾惜你病体未愈。”
被人挟制在下,还被人威胁,孟绪有些委屈:“妾只是想与陛下好好谈事。”
再说,哪有人将后来居上用在这种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