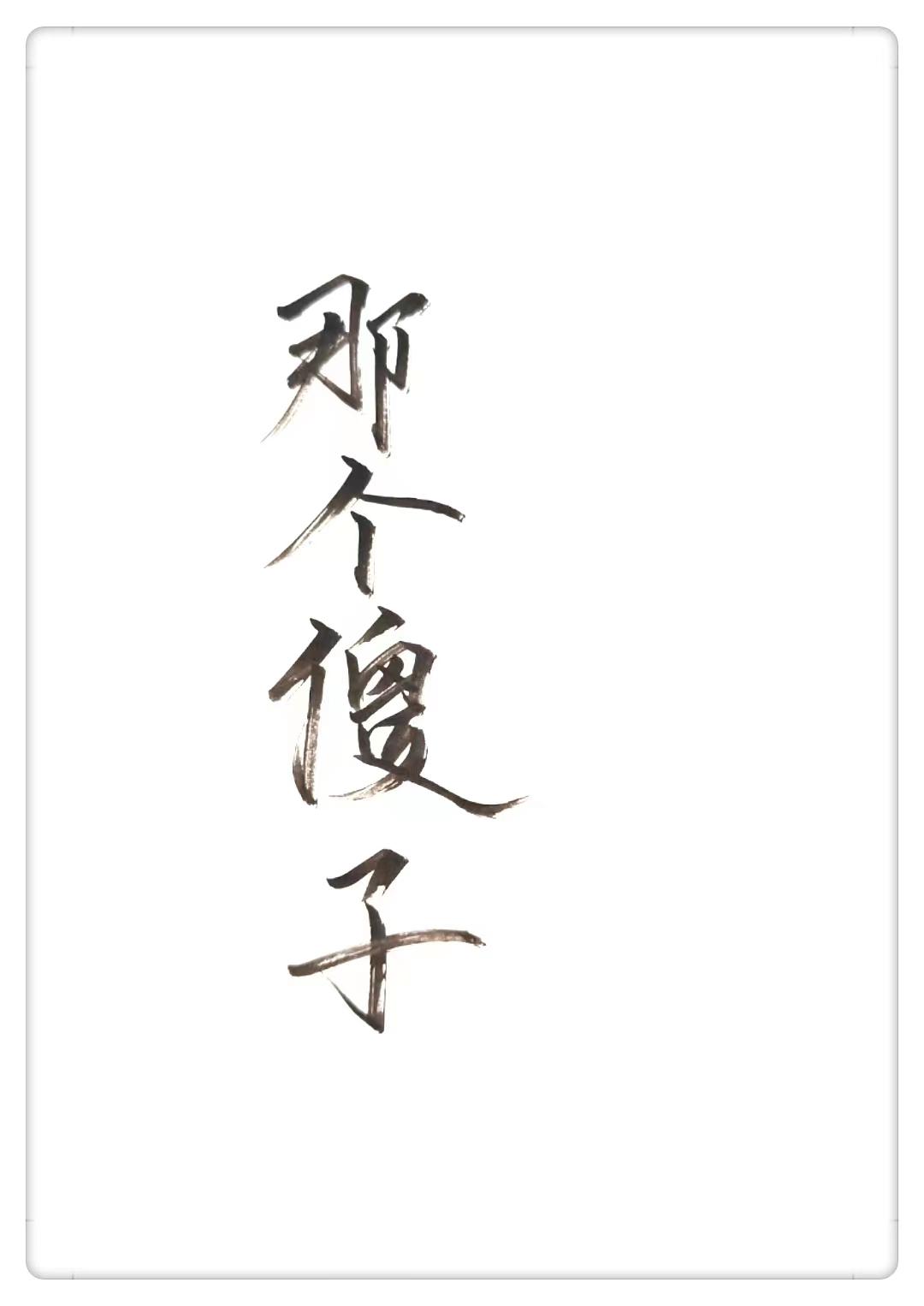69书吧>锦衣之下是哪一年播出的 > 番外一(第2页)
番外一(第2页)
近黄昏时,岑寿匆匆来报,说已经有人来传话,说是要先收到银子再给布防图,开价五百两。要求把银子在戌时放到土地庙里头,然后站着金水桥头等候,自然有人会把布防图交到手上。
“五百两,倒是个实诚价。”
6绎冷哼了一声。
他遂命人装了一箱子石头放到桥洞中,然后埋伏在附近,牢牢盯住。果然到了夜市正热闹之时,一名头戴飘飘巾身穿三镶道袍,手中还拿着一付赛黄金熟铜铃杵的算命先生晃悠到土地庙附近。
那土地庙颇小,只有半人来高,算命先生趁旁边无人注意,伸手去摸。原本埋伏在周遭的锦衣卫料定就是他,冲出来欲擒。不料这算命先生看似文弱,功夫却是不错,当即打翻两人,夺路而逃。
京城夜市颇为繁闹,人群挤挤挨挨,算命先生混入人潮之中。侯在旁边酒楼内的6绎听到禀报之后,再赶到街上,已失了他的踪影,只能分头沿着大街一路搜寻下去。
6绎一直追至金水桥头,忽在嘈杂声中辨认出铃杵的响动,循声望去,果然看见一飘飘巾鬼鬼祟祟混在人群中。他消无声息地挨近,看清算命先生肩部衣袍有被撕扯过的痕迹,脖颈还有一道带血的抓痕,显然是方才与人动手所致。
算命先生甚是机敏,6绎虽未穿飞鱼服,但一挨近,他便本能地察觉到危险,往前疾步行去。
见6绎跟上,他见势不妙,手腕一抖,匕隔着衣袖朝6绎刺来。
已经能确定是此人无疑,6绎懒得与他纠缠,一脚便将他踹飞出去。这一揣不要紧,只听见乒乒啪啪一连串声音,木头与碗碟的碎裂声兼而有之……
想是撞翻了什么小摊子,6绎抢上前,正看见算命先生扬起匕朝一位姑娘挥去,幸而她躲得快,只被削去半幅衣袖。
恐算命先生再伤无辜,6绎飞腿正中他胸膛,直把他踢得口吐鲜血,双手撑地勉力支撑着。
“说!把密报藏在哪里?”
一脚踏上他持匕的手腕上,稍稍用力,算命先生便再握不住,匕脱手而落。
他颇嘴硬:“……不知道。”
6绎再稍加气力,算命先生的腕骨在他脚下格格作响。
“我……真的……不知道!”
算命先生的声音已是凄厉之极。
当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6绎目光闪过寒芒,五百两银子就肯卖的情报,这会儿宁可废了手都不肯说,正待再给他些颜色瞧瞧,旁边忽有人插口。
“不知这位算命先生所犯何事?便是要审讯也该……”
“官府办案,闲杂人等让开!”
办案时最不喜人多事,6绎露出系在腰际的锦衣卫腰牌,示意旁人退开。
见着锦衣卫腰牌,果然围观众人各作鸟雀散,那地上的算命先生看见锦字腰牌,面色大变。
岑寿领着几名手下匆匆赶到,向他禀道:“大公子,曹昆已死。”
想是动刑时手下没个轻重,6绎暗叹口气,偏偏这时又听见方才多事的女声,声音里头还带着些许哭腔。
“官爷,你们办案也不能砸了我的摊子啊!”
6绎之前便已看见地上被砸的豆干摊子,尚冒着热气的豆干和各色酱汁洒了一地,他不堪其烦地皱了皱眉头,先命岑寿将算命先生押回诏狱。
知晓诏狱之恐怖,加上刚刚听说曹昆已死,算命先生自是不愿被折磨至死,忽然猛力起身挣扎,竟不是为了逃走,而是揉身扑在那柄抹毒的匕上,不过眨眼功夫,口吐黑血,一命呜呼。
岑寿“啊”
了一声,伸手去探他的鼻息,朝6绎摇了摇头。
“搜身!”
6绎命道。
先将带毒的匕仔细包起,岑寿一挥手,几名锦衣卫上前仔仔细细地搜算命先生的身,从髻到脚底,无一处放过……
6绎凝目看着他们的动作,身后却传来低低私语。
“活做得还挺细。”
男声道。
“这有什么,熟能生巧而已,顶多也就是咱们衙门里仵作的水准,一帮子粗人。”
仍是方才的女声,语气却已大不相同,带着些许轻蔑,“咱们衙门”
四个字引起6绎的注意。他突然意识到她的声音有些许耳熟,微微侧头……
“6大人,没有!”
搜寻结束,并未在算命先生身上现他们要找的蓟州布防图。
6绎微微皱眉,眼下曹昆与他都死了,却找不到布防图,着实麻烦,身后却又传来窃窃私语。
“你猜他们在找什么?”
说话的应该是站在那姑娘的高大男子。
“这还用说,肯定是关系国家大事的大案。”
声音虽轻,仍可听清大案两个字被她故意拖得又长又慢,显然对锦衣卫有讥讽之意。此时6绎已经想起,这个声音的主人正是今日在六扇门内押着曹昆不肯放人的女捕快,怪不得她对锦衣卫颇有不满,只是这豆干摊子跟她又有何关系?
6绎侧头瞥了她一眼,直至此时他才看见她生得颇为清秀,双目灵动之极,倒与他预想中的女捕快不太一样。
她立时朝他诚恳道:“官爷,我这些豆干其实不贵,您给个二两银子也就够了。”
岑寿上前:“两个人都死了,又找不到图,都督那边……”
6绎正待开口,便听见她居然在此时提高了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