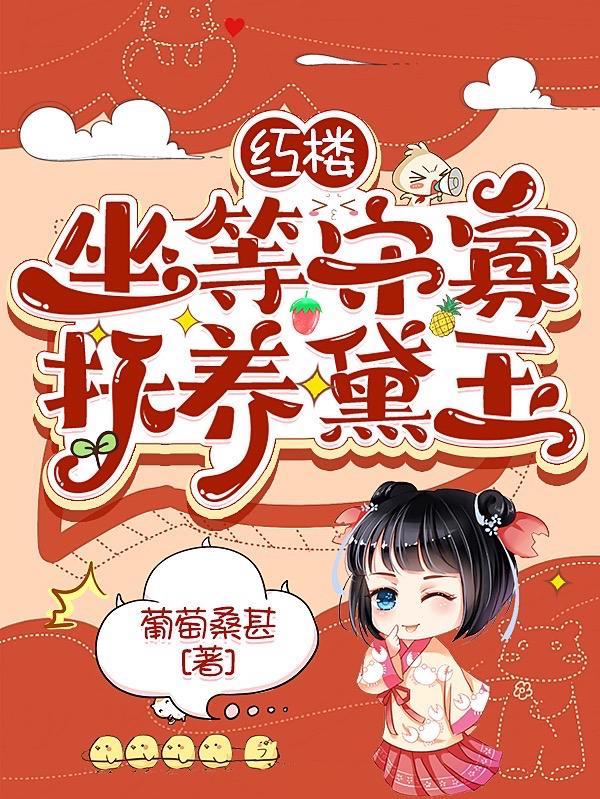69书吧>指间流沙番外在线阅读 > 第46章(第1页)
第46章(第1页)
流弋的身体比廖冬想象的还要差,瘦弱的少年满头冷汗,脸色苍白地挣扎,根本用不上多少力。但是他也不太敢强制用力,感觉男孩的身体就像破碎零件的组合,稍微不小心就会碎成一地。他等流弋安静下去,发现已经晕了过去。
最后还是进了医院。
手腕上插着点滴的管子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床边的孔文正在吃一碗泡面,看见他醒过来就很咋呼的叫了句,“操,你再不醒我都得住进来了。”
含在嘴里的面差点喷在他脸上。
流弋撑起身体坐在床上,故态复萌的呆了一会儿。身上穿着那种常见的条纹状病号服,身后感觉也也上了药,他就知道只要进医院就肯定会被发现。
“你不是病傻了吧?还是肚子饿了?”
孔文拿着塑料叉子在流弋眼前晃了晃,“我让冬哥给你带点吃的来,他早上刚走,把我丢这里先照顾你。”
“你知道了吧,我是同性恋。”
流弋忽然开口,暗哑的嗓音听上去有些刺耳,脸上的肌肉也还很僵。
“哦,这个啊?”
孔文不以为然,“你不是早就和我说过了?就是上会喝醉那次。”
“……”
孔文看他古怪的表情,疑惑道“你是怕冬哥知道啊?我跟你说,冬哥其实也和男的睡过的。前两年有个男孩子特别喜欢冬哥,整天死缠烂打的,弄得我们其他人都有点厌恶。他人长的挺漂亮,又瘦又小,笑起来跟女人一样媚,每次吃饭喝酒都很爱撩拨冬哥。有次在包厢里冬哥当着我们的面就和他做了,大家喝的又很高,嗑过药玩疯了,等冬哥做完了,有几个来了性致的哥们也提枪上去干了一场……”
孔文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我就是想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瞧不起你,这世道上什么没有啊,脏的臭的都是那些有钱人爱捣鼓的玩意儿,还要装逼装纯!”
廖冬是傍晚才来的医院,神色之间有些疲惫。流弋不知道廖冬做的应该不是朝九晚五的正式工作,在公寓里也没看到什么和工作有关的东西,很多时间莫名其妙地消失也不会解释。
办完离院手续,感觉已经好多了,下床时廖冬蹲在地上帮他系了鞋带。流弋看着廖冬的头顶,有些尴尬的不知所措。
廖冬很自然地把他抱下床,问他,“可以自己走吗?”
“没事,我自己走。”
晚饭是一桌子的清淡食物,流弋动了动嘴唇还是没说出话来。
最后反而是廖冬开了口,“那个人是谁?是强|暴吗?”
“不是。”
挤出这两个字后流弋就彻底沉默了。不是因为难以启齿和隐晦,只是不想和别人说起叶阡程。他习惯了把叶阡程隐藏在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地方,这样他会觉得安全些。
结束于开始
流弋是周二才去上课的,找了一个借口跟班主任请假。
办公室里穿着皮夹克,行事风格怪异的中年男人和常见的那种刻板老师一点关系都搭不上,对面前的男孩除了有成绩要求外也没精力关心其他。
学生通讯录上只有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不来上课就是杳无踪影,从哪里联系都无从下手。这要多坏的人际关系才能一个朋友都没有?班主任听完解释,挥挥手直接让他出去了。他实在不喜欢看男孩乖顺着表情小心说话的样子。
流弋在教室里发了一下午的呆,最初那种震惊羞辱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下去。他知道逃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这么稀里糊涂地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或许他应该站在叶阡程面前,大方一点地说,喂,我很喜欢你,不讨厌我的话能试着在一起吗?
样子可能会有些难看,但是总比等来一场莫名其妙的误会和无疾而终要好。
那个混乱的夜晚不会是开始也不该是结束。最起码叶阡程不讨厌他的身体。
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流弋在心底默默地承诺。
他们本来也没在一起过,所以分开,也不会痛不欲生。
他很早就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开谁是活不下去的。爱情,说到底被他寄托了太多了,一旦被当做另一种出路,就会背负太多。他自作主张地加诸在别人身上,别人也有权利拒绝。
他对叶阡程程的喜欢,有多少是因为现实不如意的隐射呢?
他自己用几年的时间堆砌了一个完美理想的世界,然后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放进去,好像这样就可以屏蔽掉外界施与的残忍,然后就不会受伤。
十三岁之前他把这种感情放在廖冬身上,渴望得到庇护。然后是叶阡程,唯一不同的就是叶阡程更不真实,他只能站在一边观望。这样的期待,累积的太久就会很害怕失望。
他在一班必经的楼梯口等叶阡程,喧嚣的走廊很久之后才安静下去,偶尔有人窃窃私语地看他一眼。流弋预习着要说的台词,心跳的很乱。时间的漫长已经变得没了意义。
这一次,只是把等待换成了另一种方式。
流弋没等到叶阡程,等来的是林锐。
廖冬从电梯里出来出来时遇到一个男生在楼道里徘徊,像是在等人。
男生听到动静往他这边看过来,两人的视线很自然地对在一起。
廖冬刚从外面回来,头发被吹的有些乱,搭配着硬朗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很有些压迫和不善。
他打量了面前的男生一眼,十六七岁,俊美斯文,一身低调的名牌掩映着散漫的气息,从里到外都透着一种冷淡的高贵。
那种天生的高贵让他微微厌恶,眉毛轻轻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