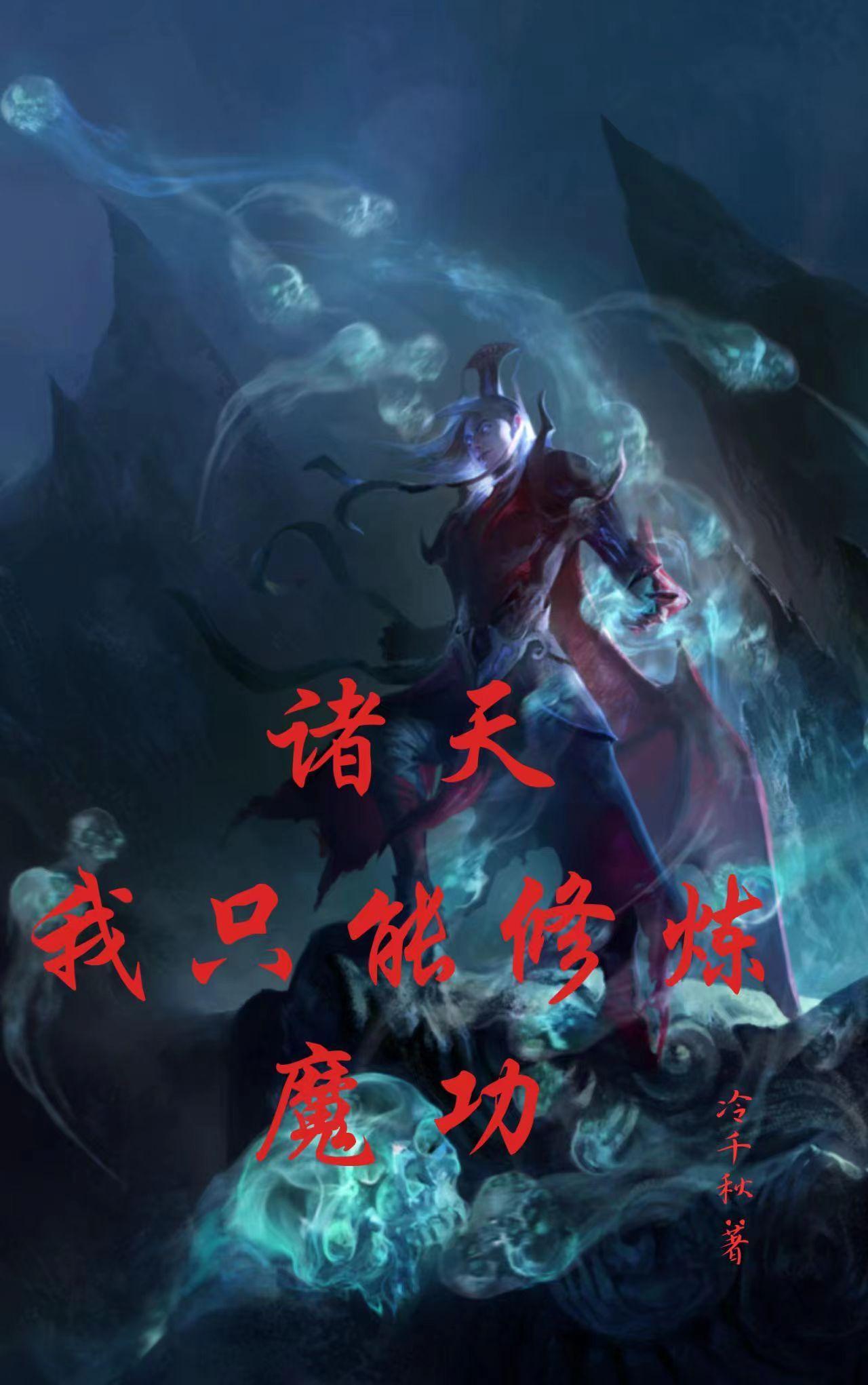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宗亲家的小娘子 荔箫 > 第97节(第2页)
第97节(第2页)
——至此,最要紧的事项算是基本定了下来,可谢迟要忙的事远还没完。
院判提出要先从惠民药局拨一批能防疫的药下去分发民间,然后便和太医们议了一番用什么方子。最后他们写了三种药方呈给谢迟,众人又一起估算拨多少合适、需要多少钱款来置办药材。
其中间或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小事横插进来,等到太医们从吏部离开,谢迟一瞧天色,恰是正晌午时。
——也就是说,他们不知不觉地忙了一个通宵,又一个上午。
谢迟不禁长松了口气,谢追自己动手沏了盏新茶,一边抿着一边跟谢迟和谢逐说:“去我那儿吧,吃些东西再歇一歇,下午再接着忙。”
谢逐疲惫地应了声好,谢迟却摇头:“不了,我得去看看谢逢。昨天给他家里传了话,说我很快就过去,没想到会忙这么久。”
他还以为最初的这点事宜不出俩小时准能说完呢,真没想到会忙到现在。
多亏他添了个心眼,嘱咐御令卫去时直接说一声是他安排的,不然以谢逢现下的境况,家里恐怕又要提心吊胆了一整天。
谢迟于是策马直奔谢逢府邸,听说他来了,胥氏便亲自从府中迎了出来。
其实胥氏作为女眷直接见他并不合适,先前登门拜访,她们也都是见的叶蝉。但眼下谢逢病着,没人能替他出来,让下人出来迎贵客也不合礼数,胥氏不亲自来便没人能来了。
谢迟见到胥氏一时略有点不自在,胥氏倒是大大方方,不卑不亢地把他往里请。
二人进了谢逢所住的院子,胥氏请他稍等,然后先一步进了屋去,请南宫氏避了出来。
南宫氏遥遥朝谢迟一福,就和胥氏一道走了。谢迟目送她们出了院门,便迈进了门中,赵景迎到了外屋:“君侯。”
谢迟颔首:“怎么样?”
赵景沉了沉:“虽尚不知这回的时疫有何特殊症状,但四公子这病却不像时疫。主要是……家人最初不知时疫这事,夫人、侧夫人还有不少下人都与四公子直接接触过,到现在也不见有人病发。”
二王那边的两个小儿子却是很快就没命了。虽然幼童体弱,在病中总比成人难熬,但也由此可见这次的时疫是急病。
谢迟不禁奇怪:“那怎么退烧那么困难?说是外头的郎中治不了,才叫你来的。”
赵景哑了哑:“四公子身上积攒的伤病,实在多了些。”
谢迟微惊,赶忙追问。赵景说谢逢身上淤伤摔伤有几十处,虽是瞧着都不严重,但积了这么多,在小的问题都攒成了大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寒气积攒在体内,只不过他年轻能扛,一时没发出来。
眼下突然病来如山倒,是因为昨天被泼了一缸水受了寒,还叫那大瓷缸砸了一下后背,身体一下就撑不住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迟听完,反倒松了口气。那些淤伤摔伤定是御前侍卫操练时留下的,他也经历过那一道,大致清楚轻重。
谢迟便示意赵景在外稍候,径自进了内室,定睛一看,谢逢躺在那儿发着愣,双目圆睁。
“醒着啊?”
谢迟笑了一声,走到床边刚坐下,便闻谢逢颓然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洛安闹时疫了你知道吗?你这倒不是,真命大。”
谢逢静了一会儿,目光看向他,很疑惑地道:“哥,我是不是……挺没用的?”
谢迟微怔:“怎么这么说?”
“背了冤屈我没能跟陛下解释清楚,丢了爵位我便不知该怎么办。兄弟帮我安排个差事,我还刚几天就撑不住了……”
谢迟摇了摇头,温言道:“前两样不怪你,后一样你也实在不必想太多。御前侍卫的差事本就苦,谁都难免病上几场,刚最开始时尤其容易不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