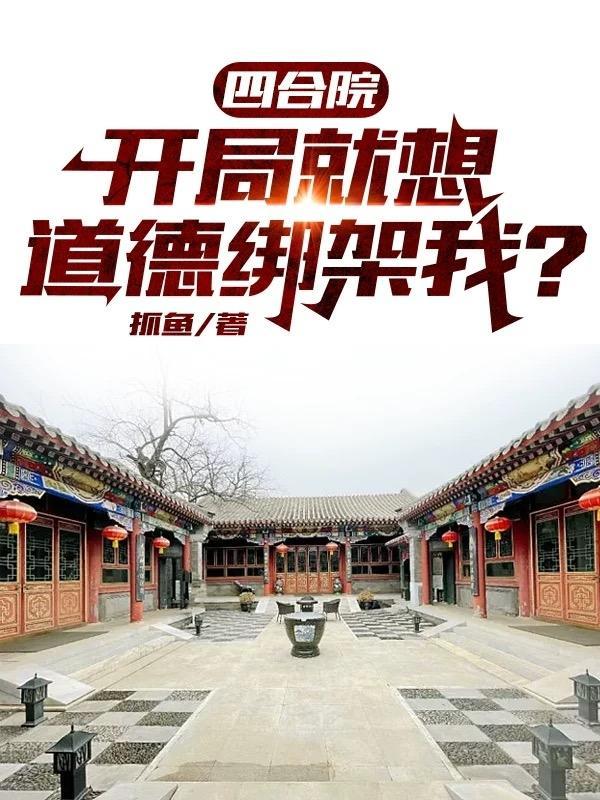69书吧>天道是什么时候进去的 > 第34章(第2页)
第34章(第2页)
与当年她年轻的“母亲”
一样,逃离这座牢笼。
她再也没有回过出生的地方,靠着资助与打工赚来的钱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每次家长会,她一个人坐在本该由家长坐的位置上,事实一遍又一遍提醒她,她不一样。
这只会推动着她离地狱越来越远。
高考出成绩那天,她照着往年的录取名次对了又对——沪都大学,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院校,也是分数范围内离那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最远的地方。
她并不知晓自己只是从一座深渊翻入另一座深渊。
所以,当她有一天突然被“母亲”
找到,说要让她改姓顾……她竟也没有太惊讶。
姓名本身带着一个家族的耻辱。
她拒绝顾惜的嘘寒问暖,骨子里的警惕感让她意识到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从天而降的东西有着难以承受的代价,她早知晓,从拥有生命的那一刻便知晓。
她了解自己叫了多年母亲的女人,多年前的伪装跨越整整十六年的距离在如今仍旧奏效。以至于终有一天顾惜再次找到沪都大学来时,她冷漠地打量着对方光鲜亮丽的着装,说:
“你还是跟从前一样,”
她观赏着顾惜几近碎裂的面具,觉得有些好笑,“我不明白,你还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她以为自己一无所有。
隔着十六年,从牢笼中拼命逃出的人们在另一隅深渊沉默相望。
这一次,孤身一人的她仍旧没有能力反抗。
她不会做徒劳的努力,而是麻木地接受安排,与根本未曾见过的、据说是顾惜儿子的男孩“换了眼睛”
,随后像一只破布娃娃般被丢弃,失去了所有的利用价值。
她隐约知道这并非是人类现有的任何一种科技手段,眼球的剧痛让她接连几个月都备受折磨。视线中的世界一日比一日模糊,她甚至不知道失明是否是最终的结果。
或许比这更坏呢?
她由于无法选择出生的命运而欠顾惜的,如她所言,都还清了。
所以当又一次,顾惜找到沪都大学的宿舍来时,她再没掩饰不耐烦的神色。
“你到底想要怎样?”
面对她突然提高的声音,顾惜似乎愣住了。
她看不清她的脸,自然不知道她面上哀怨、急切……复杂的神情,无论如何,这些情绪的对象都不是她,这一点她深有自知之明。
“我以为我们已经两清了,不是么?”
她坐在宿舍床下的椅子上,模糊感觉到顾惜站在自己面前,挡住了微弱的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