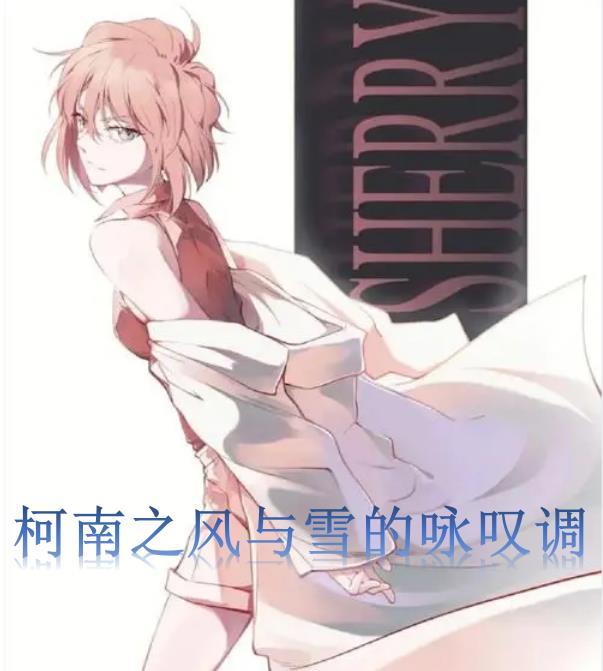69书吧>楼空春色晚(重生)伏寒 > 第28节(第2页)
第28节(第2页)
李燕燕病倒了。
白石山上最接近于郎中的人,莫过于范殊,范殊给李燕燕诊过脉,颇为吃惊,随后眉头皱起,沉吟不语。
因为范殊把郭长运留在涿州的事,古英娘这两天都没给范殊好脸色看,这会儿见他沉默了许久,终于耐不住性子问:“到底怎样嘛?怎么不说话?”
范殊看向榻上的李燕燕,女孩只一张小脸露在外头,纤长的眼睫微微颤抖,甚是可怜,叫他心头一软,讲话音调都放得不能再轻。
“我本来以为阿蕊姑娘只是旅途劳累,又遭受惊吓,一时突发头热……可看这脉象……外在是伤寒热病,内里却是气血虚损,五劳七伤,思虑过度,竟是个积年的病症……”
范殊挑拣着词句,每说一两个字就顿一下,生怕惊到病榻之上虚弱的李燕燕。
年纪轻轻,如花朵初绽的女孩子,在范殊想来应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可她竟有这样的病症,着实在范殊意料之外。
“号完脉了就让开点。”
岑骥走过来,一脸不悦,手里挥动着浸了冷水的软巾,几滴水甚至溅到了范殊膝盖上。
范殊似乎很怕岑骥,忙从条凳上站起身,拘束地退后两步。
岑骥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将软巾按在李燕燕额头上,才又转身对范殊说:“你给人看病总这么磨蹭么?该怎么说怎么说,这世上能吓到她的事,不多。”
“噗——”
古英娘没憋住,从鼻孔里漏出声笑。
范殊被岑骥说的脸热,都不敢再去看李燕燕,低着头说:“寻常发汗散热的药,别说山上一时凑不齐,就算有,也不好随便用。药方……还需斟酌斟酌。”
他为难地笑,“其实阿蕊这虚弱之症,没有药到病除的方子,根本上是要靠补益,巩固根元,常年服用人参,饮食上用五谷五菜、五果五肉慢慢调养……寨子里哪有这些,只能先调些酸浆、灯芯草、桃叶、枣叶之类的,水煎了用下,先把热火泄了吧。”
古英娘听了,叹气:“阿蕊,你得的还是个富贵病。”
听到“人参”
,岑骥意味深长地瞧了李燕燕一眼。
李燕燕无比坦然,缩在被子里,好像真的在认真听范殊讲话,范殊说到为难处,她还跟着叹气。
一脸遗憾之情。
岑骥皱眉,“嘁”
了一声,问范殊:“那你说说,要是有人参,该怎么用,和你开的药有没有什么冲突?”
范殊还没说什么,古英娘先奇怪上了:“岑骥,你去长安几年,口气也变大了!还人参?这辈子我能不能见到人参长什么样儿!”
岑骥斜眼看李燕燕,淡淡地说:“先问清楚,等打下涿州,没准就有了。”
“那得等多久?”
古英娘撇嘴。
范殊已先得罪了古英娘,又惧怕岑骥,和稀泥道:“医药禁忌,想的周全些总没错。这样,我回去把细方都写在麻纸上,连带把草药配好,再一块儿送过来。”
岑骥扬眉,当是默认。
李燕燕小声说:“那拜托你了,范大哥。”
范殊都往外走了,听见这句,耳根后面“刷”
的红了,走得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