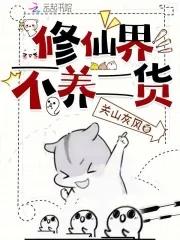69书吧>军婚娇扯好看吗 > 第22章 打你一巴掌算轻的(第1页)
第22章 打你一巴掌算轻的(第1页)
贾红梅刚二十出头,长相清秀,眉宇间带着一股傲气。
但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作,这分傲气就变成了盛气凌人。
她将秤杆掼在柜台上,出咣当的巨响。
“一篓子的烂树根,还有几大把野草,就这还拿来卖?”
贾红梅把背篓里的东西尽数倒了出来,捏着兰花指翻翻拣拣,一脸的嫌弃和不耐烦。
“当我们供销社是废品回收站啊,什么破烂玩意儿都敢往里送,不收不收,赶紧拿出去扔了!”
她掏出手帕在鼻子前挥了挥,嘴里不停嘀咕着,“什么味儿啊,难闻死了……”
祁焱将被她粗暴翻乱的草药收拢回来,脸色很淡。
“同志,这个黄棕色的是晒干摘去须根的苍术,绿色的是车前草和龙胆草,不是什么野草。”
贾红梅扭动腰肢,斜眼瞪他,“你是售货员还是我是售货员?说了不收你听不懂吗?”
真是白瞎了这一张好脸,居然只是个挖草药卖的乡巴佬,好像有条腿还是跛的。
祁焱没和她再争论,拿过背篓将草药往回装。
“诶,等等,那个是什么?”
贾红梅一把按住背篓,眼尖的现背篓里有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此时布散开一角,露出黄褐色细长顺直的根须。
普通草药她不认识,但名贵稀罕的她却一瞧一个准儿!
那是野山参!
虽然年份看起来浅,大概几十年左右,但根须上还沾着土,肯定是新鲜刚挖出来的,拿来炖汤是最补元气的。
贾红梅的眼睛死死黏在那截参须上。
她有一个处了两年的对象,父亲是机械厂的六级工,一月能拿七十多块钱工资,母亲是纺织厂宣传处副主任,待遇也非常好,关键是他们家里只有她对象这一个儿子,上头有四个已经嫁了人的姐姐帮衬着。
别看她现在在供销社当营业员,风光体面,但她只是个临时工,转正的事还得靠对象家里帮忙。
可对象的母亲一直都不太满意她,听说私底下还在托人到处相看条件更好的姑娘。
前两天对象母亲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断了腿,元气大伤,若是她能带着这根人参去医院探望,对象家里肯定高兴,说不定这门婚事就稳了!
贾红梅当即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留下这根野山参。
她抓住背篓不撒手,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同志,有事好商量,刚刚是我眼花了,你说这堆树根是叫什么苍术是吧,没问题,我可以做主全部帮你按二等价收了,只不过……”
她眼珠子转了转,压低声音道:“你那蓝布里包的是党参吧,我愿意出五块,不,十块,你私下换给我,以后只要你来卖草药我都收怎么样?”
党参和野山参虽然都叫参,但价格差了五倍不止,遇上有急用的,五六十年年份的野山参能卖出小一百的价格。
这个乡下汉子寡言少语,穿的衣服也打了不少补丁,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估计也分不清党参和山参的区别。
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十六块左右,能给他十块已经很不错了。
贾红梅神情舒展,仿佛那颗野山参已经是她的囊中之物。
谁知对方看都没看她一眼,直接拒绝道:“这个不卖。”
祁焱将野山参重新用蓝布包好放进背篓。
贾红梅见他不像在说笑,顿时急了,“我秤杆都准备好了,你怎么能说不卖就不卖!?”
错过这根野山参,她短时间上哪儿再找一根去!
说着竟直接伸出手朝蓝布包抓去。
与此同时,一只莹白纤细的手从侧面斜插进来,牢牢扣住了贾红梅的手腕。
贾红梅扭头看向这个突然出现的漂亮女人,心里下意识升起排斥和厌恶,嗓音尖利道:“你是谁,放开我!”
姚幼宁才不怵她,手下用力收紧,“要不是门头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我都要以为这里不是供销社而是什么土匪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