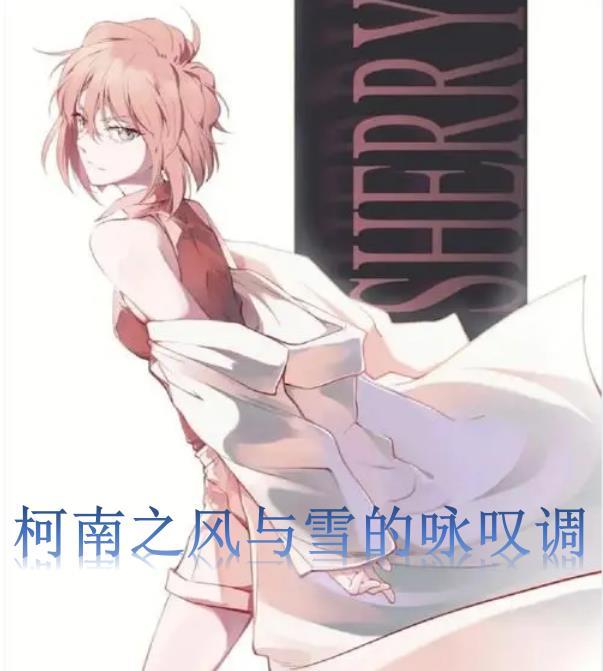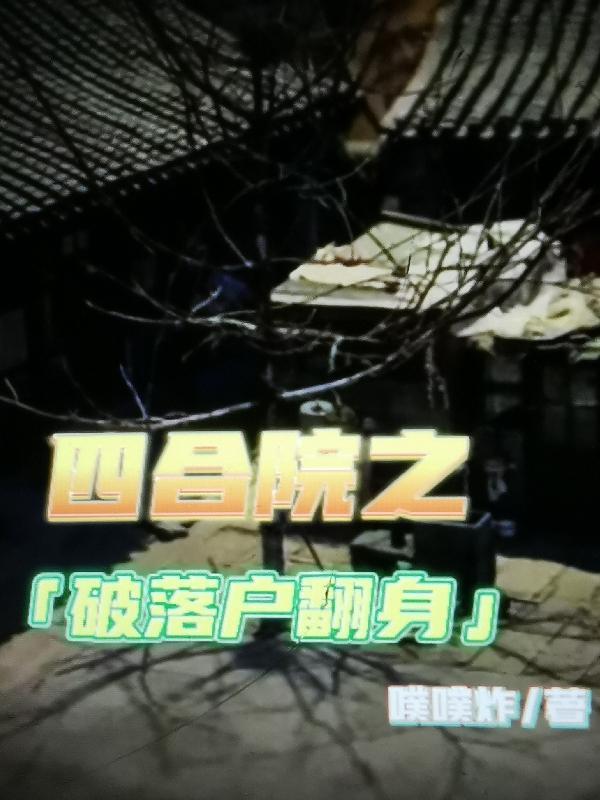69书吧>白蔷薇什么意思 > 第16章 陷入梦境(第2页)
第16章 陷入梦境(第2页)
不适地眨着眼睛,用手抹了好几下,但那种刺痛的感觉仍然存留。
荒谬。
太荒谬。
1972年怎么会出现蛇怪?萨拉查·斯莱特林的继承人从来都只是汤姆·里德尔,怎么会是他亲手打开的密室?现在的“伏地魔”
正在迅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不会将眼界仅限于霍格沃茨。1992年……
手袖突然松松垮垮右手变得瘫软无力,我看着羽毛笔滚落下桌,在空中的停留时刻,慢放、拉长,与宾斯教授的音、顿挫一致。
我像是忽略了某个事情,明明是一些黄油曲奇的碎屑,一些看起来影响甚微的事情,一些我不会去注意的时刻。但那些事情是什么?陷入了某种死循环,我强迫自己弯腰捡起记忆的碎片,但是我不行,头痛欲裂。我扶住自己的头,一边偏向左边静静躺在地上的羽毛笔。视野中的手指忽远忽近,在空中垂下,捉空,空气从我的指尖逃离从我的指间躲过。
“嘭!”
应声倒下,木椅与我。
身体没有摔得粉碎,但我的鼻子中不断涌出液体,我神智不清地望着那一只羽毛笔,混沌的环境之下它是如此安然。
无力地向它伸手,却看到它被无数个黑影踩住,最后黑影覆盖了我的双眼,直至把我吞噬。
我躺在一片空白中。
渴望着永远就这样瘫软在地上,永远不会有变化。
我将双手附着面部,指缝露出的光束混入了温热的肉色,我的眼睛胀痛,却能够勉强接受,透过光束我的脑袋中闪现出许多被裁剪过的回忆。当你拼好千块的拼图,却在不经意打翻后,你会在满地的狼藉中窥见自己的多种情绪。慢慢拾起,却唯独找不到最关键的那一块。尽管你去照着它轮廓重新制作一块外表别无二致的拼图,再贴回原来的整幅拼图时——
它回不到之前的样子了。
睫毛被沾湿,指腹被沾湿,耳朵被沾湿,丝被沾湿。
我慢慢坐起来,摩挲着空荡的一切。一个身影,同样坐了起来,摩挲着空荡的一切。
我问它,我该怎么办。
它问我,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不知道。
它说,你会知道的。
我看着影子随着我和它谈话的加深而越来越完整,最后与我完全相似,但我和它知道,我们两个就像相似的拼图,永远代替不了对方。“我会帮助你的,”
它如是说,这让我觉得身下的地板越来越真实,“你也会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