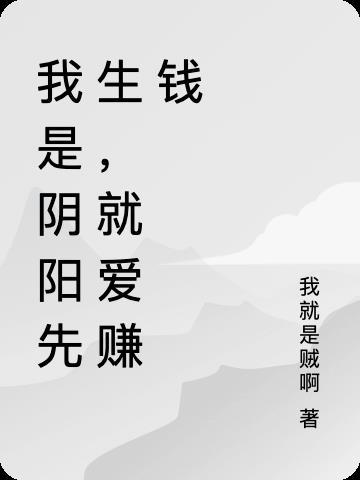69书吧>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怎么翻译 > art2 男人和你好(第1页)
art2 男人和你好(第1页)
我给林禅语发消息:酒吧老板有点变态。
凌晨三点,我走过的城中村里基本家家户户熄了灯。姜黄色的破损的窗户沙沙,间或有女人的叫声,我脚踩在有裂纹的水泥路上,不知道他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窗的吱呀声更响,风突然有很多存在感,空气变冷。我抬头去看天,不期然有一撮烟灰落在脸上。
“小姐。”
三楼打开的窗户边有一个穿背心的中年男人叫我,“200块要不要?”
夜太黑,我看不清人,伸手将脸上的灰掸掉。中年男人吹起口哨,又追加:“250块要不要?”
他的语气太恶劣,我边摇头边快走。天上的雨就那样恰时地落下来,将所有声音变得朦胧。“臭婊子。”
我只听到这个模糊的词,豆大的珠子打在脸上。我抹了把脸,把手机揣进包里。
搭建的泡沫彩钢瓦屋顶上传来很大雨声,轰隆隆的震得人耳膜疼。山林里下雨时没有这样暴戾,语文课本里有记录:大铉嘈嘈如急雨。
那乐器传来的是这样的声音吗?
水泥地的凹面聚出水洼,吐出一个又一个大的泡泡。我提着有跟的鞋子赤脚踩在水下,感受到白天里被太阳照热的水泥地在迅速降下温度。夏天不会冷脚,偶有细碎的石子陷进肉里,硌得人疼,很快又被落下的雨带走。
我是很喜欢雨天的,即便会淋湿衣裳。
走过小街再转五个弯就可以到家。我摇了摇包,确认有不如何清晰的铃铛响。转过一个弯,家家户户的窗陆续打成半开,又转过一个弯,高一楼有人伸出头和手。明黄色的路灯把前路照亮,混乱的电线摇动,我轻轻跳起然后踏在它们飘荡的影子上,踮起脚尖学电视里穿礼服的人转圈。
当然,是站不稳的。
没有人的街道上没有安装羞耻,我踉跄一下才提着湿哒哒的裙子定住。身体朝向变了,停下来的我面对路灯照不到的幽暗巷口。有打火机的焰光一闪一闪,像温暖的闪电。
一个男人靠墙坐在地上。
他穿着……大概是工地的衣服,背心和长裤上有很多个包。城中村的房间没有遮雨的棚,雨水也将他的头发和衣服打湿。不怎么大的火光里,有水珠顺着他鼻梁滑下,落在衣服上成小水窝。他湿淋淋的,像一只挫败的狼犬。
这是一个与朋友走散的旅人,还是一位同样远离家乡的打工者?是黑社会?还是欠债人?出入这个城中村,复杂的人总很多。我咬了咬嘴巴,还是没忍住朝前走。
随着我的走近,他也转过了头。
大约是一个很好看的男人。
为什么说大约,因为我身边实在少有五官那样立体棱角也分明的人,他更像是手机屏幕里“追忆往昔”
剪辑中的一位,但比市区巨大墙壁上挂贴着的穿西装的男人要更强壮一些。“明星”
。林禅语曾去接机,回来后她捧着脸感叹,“我男朋友也那么帅该多好。”
啊,眼前这个人应该叫帅。
因为工作,我叫过很多人帅哥,叫过很多人美女。美女很多,帅哥却并不常见。或许是因为这个,当真正给陌生人打招呼时,帅哥这个词已经不能够体现出庄重。
但我实在想捡什么人,我很早就想捡到什么人。
于是我蹲下来看他,露出一个自觉最友好的笑。
“——你好呀。”
我想想,这个人最开始和蹲下的我对视时,是带了杀气的。
轮班的姐姐妆花了需要重新化妆,我没来得及洗脸便出了酒吧,后面又下起雨。齐刘海太短,不能挡住一半时候开始斜着下的大雨。六块二三个的蝴蝶发夹搭配的是同样不怎么昂贵的化妆品,不具备任何防水功能。我在他冷漠的视线中害怕地跌倒,才隐约看见从脸上滴下来的水带点黑色。
这有一点好笑,我顾不及对面人的态度,就势坐在地上,在他的注视下认认真真用屈起的手兜着下巴。脸上的水掉进人为制造的凼处,路灯下它果然是混杂的灰色。
“抱歉。”
想到自己可能有的样子,我没有忍住又笑起来。陌生人的确很难对一个双眼像熊猫、眼线乱流、着女人裙子却又是男性声音的奇装异服者没有戒心。我抬起头,就着雨水将脸上能抹的抹掉,“因为下雨了,所以变得混乱。”
我不怎么和不认识的人寒暄,除了医生、林禅语、还有找工作时说了非常多话几乎没有什么和别人主动交流的经验。刚才的小乌龙消解了我对他的恐惧,我重新蹲起来,抱着膝盖自下而上看那个陌生男人。
我希望他能和我主动搭话。
“不必抱歉。”
他在雨里回应我,“我没有害怕。”
“下雨了。”
我继续看着他,“你不回家吗?”
提到“回家”
两个字,他似乎稍微皱了一下眉头。我不能读懂他脸上的情绪,只肤浅觉得这张脸应该是林禅语口中的“真帅”
。或许是探究的眼神太露骨,男人收了打火机。
“家太远。”
他回应道,“所以决定不回去。”
这是个头脑清醒的男人。
租住在城中村混乱区域的边缘,我在替班回家时会遇到一些同样坐在地上的人。有比我小的小孩,有头顶没有头发的中年人。我想捡年龄不大不小的成年人,但或坐或倒的人里面,不是醉鬼就是毒品上头的瘾君子。
“你是黑社会吗?是毒贩吗?”
我突兀地发问,男人显然愣住了,但我还在继续,“或者被人追债、是正被抓捕的潜逃分子?”
“对不起。”
我看着又皱起眉头的他,眨眨眼睛,“我应该问得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