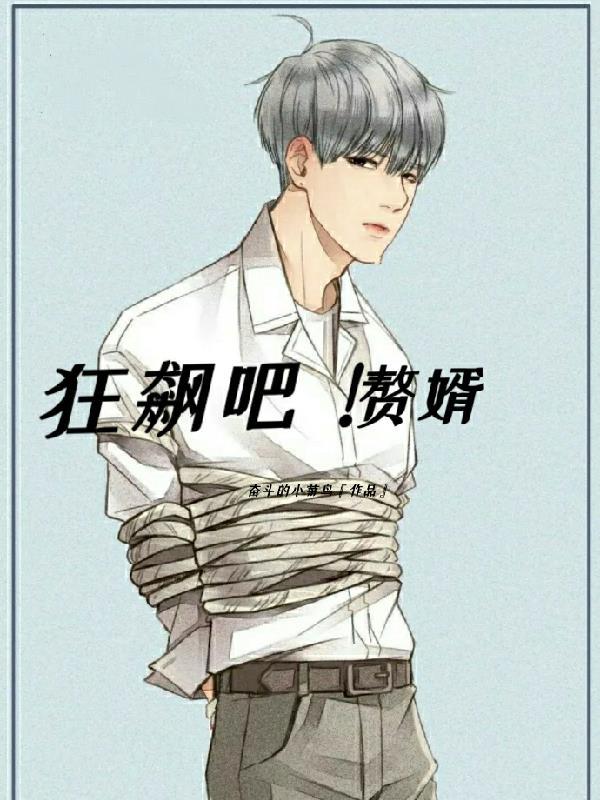69书吧>被顶流退婚后我成了他的白月光百度 > 第25页(第2页)
第25页(第2页)
班主任又开始挥教鞭了,“我让你看他,没让你看地!”
贺秋渡海拔太高,林杳然只能把头抬起来,才能堪堪与他对视。但对方只要稍微垂下眼帘,就能把他整个儿收拢眼底。
视线穿透厚重的镜片,林杳然能明显看到贺秋渡眼中泄露出的笑意,仿佛非常享受被他用上目线的姿态注视。于是他不甘示弱地回瞪过去,对视了一会儿,却又先败下阵来。
是被迫地,也是不受控制地,他无法遵从自己的心意,就这么落入贺秋渡的眼睛。贺秋渡的眼睛黑曜如星,仿佛具有虚化周遭一切的能力,引得人再看不见其他,一脚踏空般跌进无边无际的旋涡之中。
太狡猾了。林杳然想。
林杳然难过地想。
心思一旦被分散,他竟暂时忘却保持抬头的动作,会让帽子难以觉察地向后移落。一小绺黑就这样趁机从帽檐底下钻了出来,仿佛遭受压迫已久的某种奇异花蔓,迫不及待地要让某人窥见它的美丽。
教室后排的窗口送进一缕恰到好处的微风,它便借着力,勾缠住林杳然的耳朵,梢戳在柔软的耳珠上,深浓的黑与霜洁的白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最不可思议的靡丽装饰。
耳廓忽然传来熟悉的热度,他还没反应过来,温热的指节就已经掠擦而过,替他将那绺不听话的黑捋到耳朵后面。
“头,掉出来了。”
贺秋渡淡声道。
林杳然根本没听出他深藏话中的复杂情绪,他的脸色一下子惨白无比,恼人的热意和晕染的薄红瞬间从身上褪去,整个人如堕冰窖。
几乎像一只逃离陷阱的小动物,他慌乱地朝后退开,一边躲,一边伸手去摸帽子。
还好,没事。
他侧过身,手指颤抖着把那绺掉出来的头重塞进帽子。
心怦怦地跳着,然后像被剪断线的风筝,滞重地往下坠落。
就算心知肚明,自己在贺秋渡眼中一定是个不怎么好看的怪异形象,他也不希望把最难堪的一面在对方面前暴露出来。
其他人都不愿意,更别说是贺秋渡。
林杳然用力咬了咬嘴唇,又往后退开一些。
脚已经开始酸痛,更难受的是后腰,僵硬疼痛,连动都不能动。
华桦曾说他二十多岁的年纪,七老八十的身体。他本就没有久站的体力,更何况精神上的羞耻消耗更大。
贺秋渡一眼就注意到他的异样,“你怎么了?”
林杳然抿紧唇角不说话。腰很痛,像沉了一块大石头,他忍住想伸手去扶的念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就感觉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起来。
“累的话,可以靠在我身上。”
耳边,传来贺秋渡压得低低的声音。磁性惑人的声线,震得他耳根酥痒。
林杳然才平复下来的心神,又被搅动得晃荡。他想再挪开一点,腰间却骤然一紧,毫无防备地被贺秋渡揽了过去。
整个人都失去重心,甚至不需要耗费一点力气去支撑自己站立,就这么完完全全地托付给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