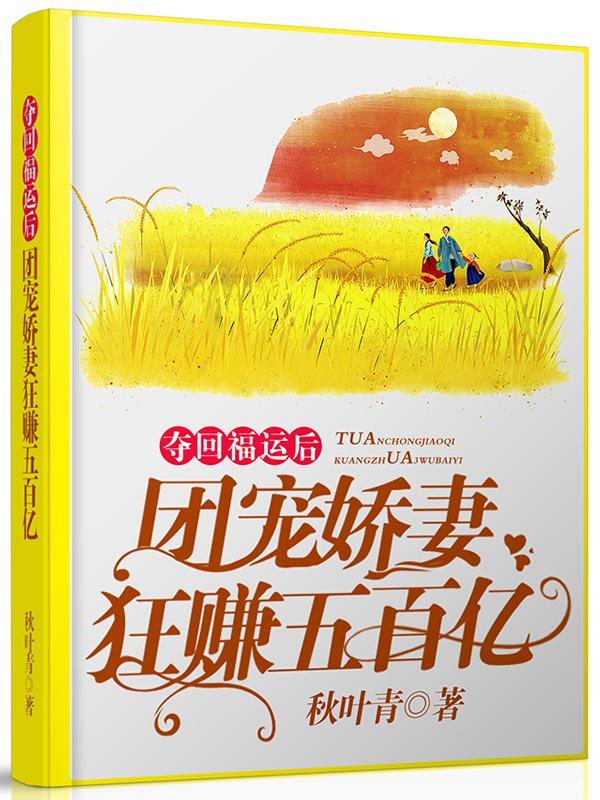69书吧>彼个所在是什么意思 > 第50章(第2页)
第50章(第2页)
你还笑的出来,不管瞭,你的狗你赶紧抱走。我一边说著一边把陈大年推到曾砚与那边。
我看它还挺黏你。曾砚与说道。
大年,你爸爸不想要你瞭,你跟我过怎么样?我看向大年,玩笑道。
它倒是一脸认真地看瞭看我,又扭头看向曾砚与,一副乖乖任我们摆佈的模样。
他爸爸不介意,你要是愿意,随便。曾砚与模仿著我的语气说道。
随便啊我喃喃道,又看向陈大年,说,你怎么不睡觉,嗯?我冲大年说道,双手不住地揉-捏起他全身的毛发,当然一定少不瞭它结实的蜜桃臀。
它倒是一副欲拒还迎的模样,让我o瞭个遍。
我摸的正欢实,甚至都快忘瞭要睡觉的事,曾砚与突然开口道,之前你问我它怎么姓陈,是你的姓。
听到的那一刻,意料之中地,我还是愣住瞭。
陈大年,其实不用想都知道陈是我的姓。
可真的从曾砚与口中听到后,那种想法从我的视角以为的变成瞭从他的视角叙述的,那意义也瞬间变瞭个样。
就像我隻是单纯把陈大年作为一个名字,他却是把名字放到瞭它的身上。
他说那时候他在拍摄《野鸟》,有隻狗突然闯到瞭他的镜头裡,淋瞭雨,全身髒兮兮,毛发和皮肤粘成一团,肉眼可见的瘦,一隻腿还受瞭伤。
他说他当时觉得那条狗和他很像,所以他给它洗瞭澡,治瞭伤,又把它送到瞭流浪狗收容所。
曾砚与说著看向陈大年,继续道,两个多月后,我就养瞭它,当时它还不到一个月大,耳朵还没立起来,你绝对想不到我决定养它的时候最庆幸的是什么。
他当时说的轻松,我听到他把流浪狗和他一并而论,心裡总归不是滋味。
什么?我附和他道。
庆幸我对动物毛不过敏。他轻笑道。
我却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他是对动物毛不过敏,可我对酒精过敏。
你当时是在想你对动物毛不过敏,还是在想我。所以我直接问瞭他。
睡不睡觉什么的在当时一点都没有他接下来的话重要。
我问他,曾砚与,你当时到底想的是什么?
我如果说想的是你,你要怎么做?他开口道,反问的语气和当年我第一次问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时一模一样。
你说瞭我才知道我要怎么做。我索性直截瞭当道。
他却又沉默瞭。
一秒,两秒,五秒他终于开瞭口。
柏儿,那些年我没少想你,现在也是,你明白吗?他看著我,语气安静又平静。
白天会想,晚上会想,做梦也会想,这话听著不像那么回事,但有段日子我真特想回来,回来看看你他继续说道。
我隻是看著他,突如其来的一段话,在黑夜的气氛和周围灯光的映衬下,像做梦般,而他的眼神中始终藏著比黑夜还要深的黑暗,我看不明白。
当时的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他消失瞭四年,又说那些年没少想我,连养的狗多半也是因为我,自始至终他都没忘瞭我,甚至时常想到我,甚至是一直都在喜欢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