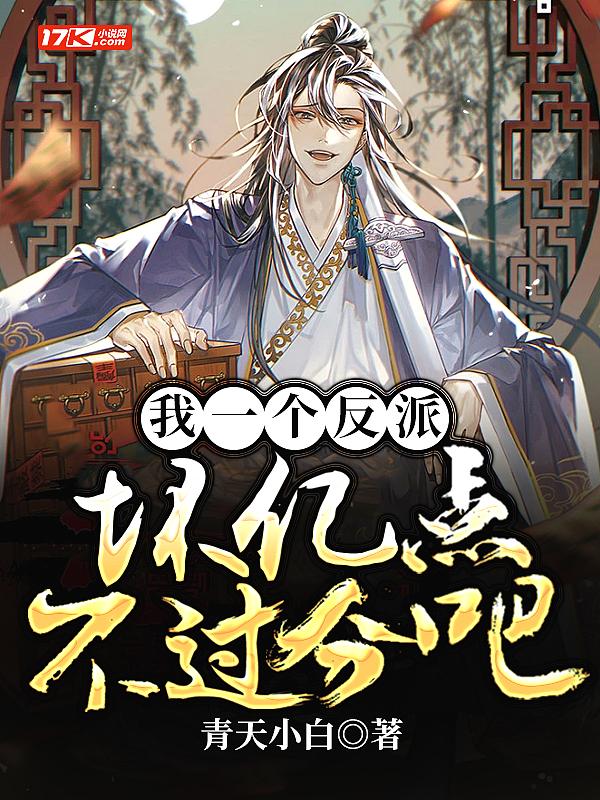69书吧>清河传芳是什么意思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她心里真是憋了不少的气,那几剑耍得干净利落,大家都四散逃了,可仍是被她抓住,通通要抹了脖子才罢休。一人哇哇乱叫着跑上坡了,白敏荷却没追,她心想:“一定要一个回去报信的,我得让那卫家、那河北知府知晓,我白敏荷可是不好惹的主!”
忽听“噗通”
一声,白敏荷惊愕回头,那小船却翻了个子,反扣在水上,而船上的人呢?早不见蹤影了!
“王小姐!”
白敏荷一跃进水中,她身上有一些伤,是打斗时划到的,因此到了水下仿佛周身有一层粉红的棉花云,是雾气,它就在水里游走,是柳絮,它就在水里飘,渐渐地,白敏荷接近了那个身影,在河水之中,那抹紫色就显得尤为招人了。
两人浮出水面,白敏荷去探她的鼻息,脸色登时一变,她搂着王延清的腰,一手划水划到船边,推着把船翻正了,她也顾不得身上的刺痛,将人带上去,划着浆就走了。
那好长的河,好迤逦的山脉,蜿蜒着是一条龙。除此之外,白敏荷想不出再华丽的词形容它,身后有一些呻吟声,她知道王延清病笃。不久,船靠了岸,从前走不远有一处村庄,白敏荷“砰”
一声踹开药铺的大门,喊道:“大夫,大夫!”
从里屋走出一位老人,白敏荷就抱着王延清闯进来了,那老大夫实在是受了惊吓,不过见着王延清惨白惨白的脸,当即明白过来,道:“你把人放这。”
他指着屋左侧那张木床,白敏荷按着他说的做了,道:“大夫,你快看看她,她额头好烫。”
那老大夫探了探她手腕,转身去药柜里抓药,边抓边道:“别急,别急。”
又急忙进了里屋去,白敏荷在此期间又摸了摸她的头,似乎是更烫了,她还总是小幅度的挪动,白敏荷侧着耳朵去听,有一些听不清的话从王延清嘴里冒出来,白敏荷只得连连叹气,她很是惭愧,道:“对不住!”
她抱王延清在怀里,右臂上包扎过的都松掉了,伤口淡淡的血腥味被河水沖散,白敏荷覆着她的手背,很热很热的,很烫很烫的,她自己的心也好像被油煎在热锅里。
醉花阴
她想着自己那时候如果没有临时回来,现在王延清已经回了王府,下一个月就要跟卫褚云成亲,不,或许婚礼会提前,又或者再拖一段时间,是下个月,也许也有下下个月,但不论如何,白敏荷可以想到结局,那就是王延清必得和一个人成亲不可。
白敏荷心想:“我无父无母,从小跟在师傅身边长大,山上除了我们也没有别人,师傅不会给我安排谁成亲,我想干甚麽就干甚麽。那麽,我的潇洒为何不能分她一点呢?”
她正想着,怀里的人又忽然哼了一声,白敏荷一惊,她向里房喊:“大夫,大夫,你快点呀!”
她说话时,那老大夫已经掀帘出来了,双手捧着一碗刚熬好的药汤,白敏荷接过碗,老大夫回身又将白蜡烛点上了,放到床边,那墙上放大了她们两人相依的影子。白敏荷舀了一勺在嘴边吹,她一只眼睛向下瞥,她发现王延清的睫毛真长,皮肤也真白,鼻子更挺,都让烛光把鼻峰的阴影照出来了,那眼皮在轻轻地抖,白敏荷又看得呆了。而后低声道:“你喝罢,不烫了。”
勺子抵着王延清的唇角,怎麽也塞不进去,白敏荷只得腰挺得直了,怀里的人也跟着坐直了一些,她将头凑过去看,看王延清有没有喝。
那老大夫道:“给她包伤罢。”
白敏荷擡头,对方拿了纱布和药酒过来,她道:“多谢了!”
她再喂第二勺药汤,又对那老大夫道:“今天可以让我们住一晚吗?”
老大夫转身回里屋去了,白敏荷知道这是默许的意思。她轻轻弯了一条腿向后靠,顾忌着王延清,挪得十分地小心,背靠在墙上时,白敏荷终于能松下一口气。在那坐了几秒,又倾身把纱布拿来给王延清包好,那药也才喝了一半不到。
于是,那天光渐渐晴朗了,床边的烛也快燃尽,那老大夫从里屋出来,他看那两个姑娘坐着睡着了,把门口的招牌拉开,这一时间他药铺就开张了。
“唔……”
白敏荷听着他的脚步声,迷迷糊糊就醒了,她本来想打个哈切,却听王延清又哼哼着,她霎那间就住嘴了。
白敏荷这一晚上都没有睡甚麽,其一是坐着睡怎麽睡,其二就是王延清总会不时哼哼着,她有时无时探对方额头没有有再烧,这天亮了又探了一次,索性好得多了,白敏荷大喜,自己下了床,轻轻给王延清放倒了。
那老大夫收拾了前面的碗,又盛了一碗药给她,白敏荷很是感动,道:“您贵姓?”
那老大夫道:“我姓陈。你把这碗药再给她吃了,等到中午就应是好的差不多了,到时候你们就走罢。”
白敏荷从卫褚云的荷包里拿出一沓银票,又从腰间掏出一个金元宝,这是她从别人怀里掏来的。道:“您拿着罢。”
陈大夫惶遽地道:“这太多了,我不能要!你们只是喝了我两碗药,也不当事,我也没说收你们的钱。”
白敏荷道:“这并不是我的钱。今年官府的经济本来就不好,人家向下征的很多税呢,咱们都是小老百姓,我师傅还说如果再没有饭吃他都要下山卖艺去了,我就是负责劫富济贫的,您不收我也给别人,就是便宜你的。”
陈大夫果然见着她腰间配着短刀,床边还杵着铁剑,他笑了一笑,就从她手上把那沓银票拿了,道:“好罢,但是我不能再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