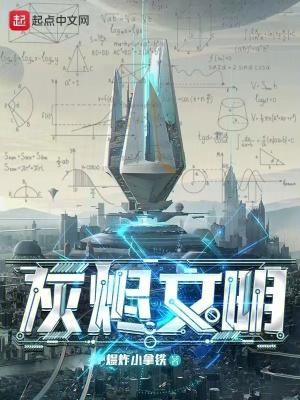69书吧>山医命相卜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夜里,乔四海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他被一团红色的雾障所笼罩,雾气浓重深厚,置身其中让人辨不清方向。不管他往哪儿走,红色的雾障始终包围着他。后来,雾气被一道夺目的白光劈成两半,他循着光前行,蓦地,花信现身迎面而来,他穿着一套黑色的练功服,后背斜插一柄古剑,姿态板正,气势凛然,颇似武侠剧里的江湖高手。
只是,他好像看不见自己,“哥,哥,哥。”
乔四海喊了无数遍,他始终置若罔闻。走进瘴气,花信拔剑目光凌厉,“这次我看你往哪跑。”
花信挥剑,招式奇特,那红雾只得闷头乱窜。下一秒,他感觉自己躺在了大街上,心脏绞痛,眯着眼,乔四海看到身边围着许多人,花信站在马路对面,神色慌乱,茫然无措,几乎下一秒快要急哭了似的。
“哥,你别哭,我没事。”
乔四海捂着胸口,呓语。
醒来时,天大亮,院子里练功的声音铿锵有力。感觉自己赤条条的,乔四海下意识抱紧了被子,看向另一侧。花信早已不在,倒是床头整整齐齐叠着一件崭新的内衣还有卫衣和休闲裤。
只是,肚子上莫名的酸疼是怎么回事?乔四海纳闷。
试了试衣服,其他倒挺合适,就是裤子短了点。乔四海顶着鸡窝样的头发走出房间,看到院里的人,迟疑不定,“你是岚姐还是岳姐啊?”
林岳瞄了他一眼,乔四海当即认出来,颔首微笑,“岳姐,早。”
他吞吞吐吐,林岳猜出来乔四海想问什么,主动解答,“花信他们去买早饭了。”
“哦。”
他乖巧地转身回房准备洗漱,唯恐避之不及,“岚姐,我先回屋,就不打扰你继续练功了。”
和殷楚风一样,他对这个林岳也没有好印象。同样是和邪祟接触往来,怎么花信和林岚这么慈和,林岳和殷楚风那么阴森恐惧呢?不过才半天没见,他心里已经开始想念笑容姣好的花信了。
再出来后,花信和殷楚风笑着回来了,手里提着小笼包,拌面还有小米粥。难得,花信没有穿一身价格吓死人的大牌,清清爽爽的白体桖白衬衫,加一条休闲裤,鞋子也是平价的款式。脖子上,围了一条丝绸的浅青色方巾,头发半扎,一派艺术的气息。
“哥,你怎么想着扎起头发了?”
他这个样子,乔四海看着很是新鲜,围着他左盯右瞧。花信模样秀丽,但一点不显得女气,反而有种儒雅风流的书生的感觉。特别是把头发束起,露出光洁的额头,直挺挺的鼻梁,越发俊美。
花信被他盯得不好意思,“我,我没洗头。”
殷楚风笑着揭他老底,“这家伙对洗发水,沐浴露,还有香水,有种莫名的偏执。从小到大,我见他只用一款洗发水,沐浴露,连香水也是固定一种香调。吃的穿的,他能将就,但是这些绝对不行。”
锻炼完,林岳大汗淋漓,擦着毛巾戏谑,“我们也就是普通的小市民,跟家大业大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花少爷可不能比,用不起他那四位数一瓶的洗发水。”
“你们说什么呢?”
乐呵呵的声音响起,一个精明强干的老人走了出来,虽然头发花白,但双眼炯炯有神。老人一身青色长袍,别具仙风道骨。
见到老人,花信恭敬问好,连桀骜不驯的殷楚风也对他敬重有加,谦逊地喊了一声“林爷爷”
。
独身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乔四海早练就一双察言观色的慧眼,紧随其上,叫道:“林爷爷好。”
“好好,你好啊。”
林爷爷笑眯眯地盯着乔四海,摆手,“过来。”
“你就是林岳说的乔四海吧?过来让爷爷瞧瞧你身上的东西。”
林爷爷和蔼地挽住乔四海的手,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式,他立刻感觉身体里涌动着一股热流,越来越热,最终集中到了手上。
林爷爷目不转睛瞅着乔四海手上的东西,砸砸嘴,“不错,就是火羯。没想到老头子我活了这么久,还能看到这么诡异的邪祟。”
松开他的手,林爷爷陷入沉思,良久,才说道:“事情吧,说难办也不难办,说好办吧还真确实有点难度。”
“爷爷,您就别卖关子了,您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林岚看不下去爷爷的模棱两可,催促。
“你这丫头,”
林清海怒瞪拆台的自家孙女,“就不能让爷爷装装样子啊。好不容易马德旺那个老匹夫有事求到我头上,我摆摆架子不行吗?”
“林爷爷。”
花信讪笑,拘谨地抿着嘴唇,看到他这副模样,林清海百感交集,“行了,爷爷不逗你了。”
“这事还得从我爷爷那儿开始说起。”
林清海找到位置坐下,追忆往昔悠然开口,“当年我爷爷被人请去除祟,回来时经过村子的一口池塘,恰巧看到上面飞着两团光,一大一小,大的是红色,小的白色,两团光相互追逐,好像是在争斗。我爷爷自知遇上了奇事,悄悄在一旁猫着偷看,后来那团白光直接把红光吞噬了,接着沉进了池塘里,再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我爷爷翻遍了书终于查出是它们是什么。”
“红色的那光,是火羯?”
林岚插话。
“没错,红色的正是火羯。”
林清海肯定道。
“那白色的呢?是什么?”
林岚感慨,“既然它能吞噬火羯,一定是比火羯更厉害的邪祟吧。”
“非也,非也。”
林清海笑着摇头,“其实啊,邪祟就跟世间万物一样,有强弱之分,能够相生相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吧,凡事讲究一个平衡,不存在完全至高无上,凌驾一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