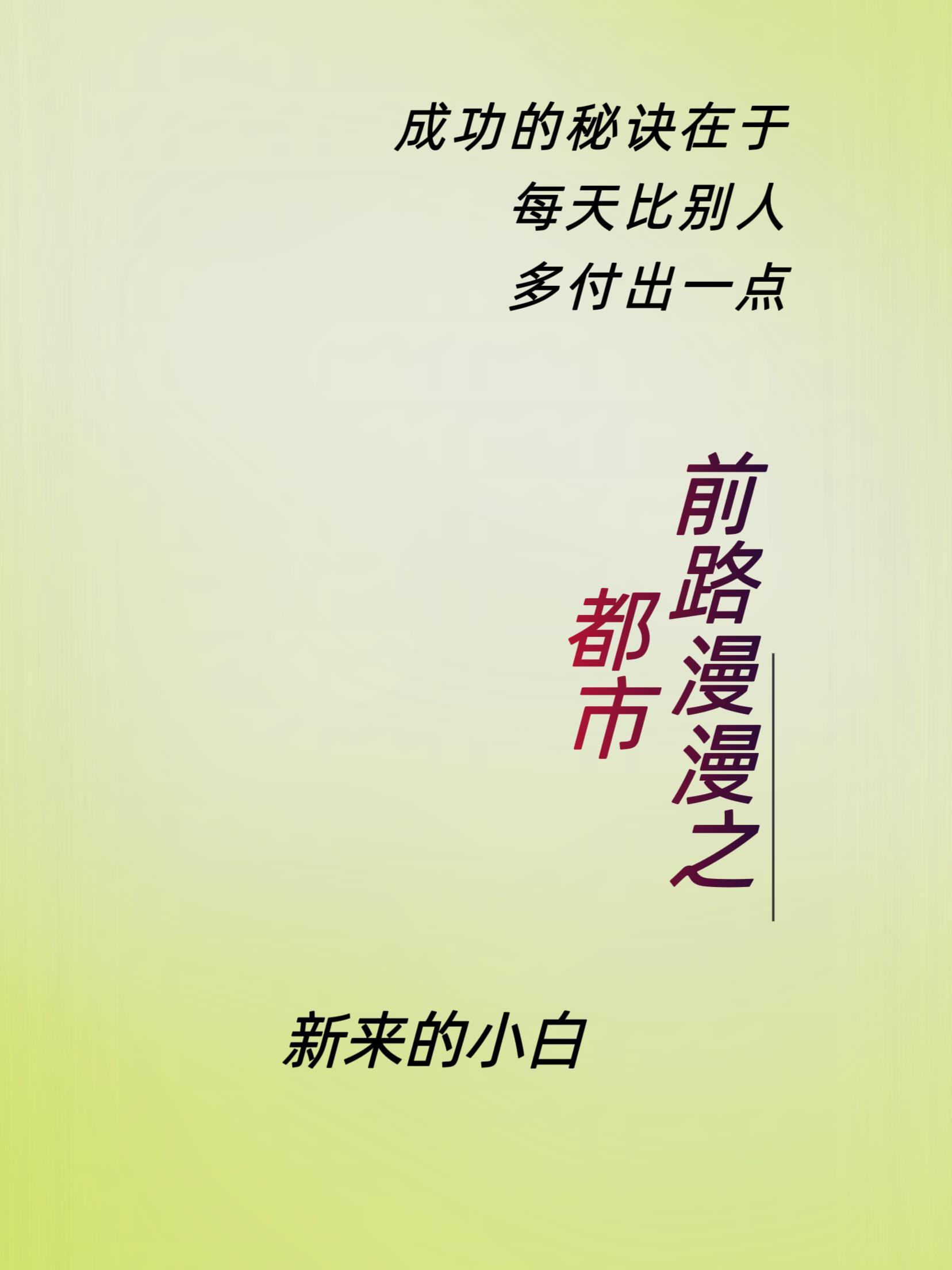69书吧>梁先生生日快乐图片 > 45 梁家同脉的血(第1页)
45 梁家同脉的血(第1页)
第一次是在镇子不远处的草场上见着他,那个上午阳光真好,有浅淡的微风。他躺在四层小楼的天台上,阖着眼的样子安静极了,可没成想醒来后是又痞又坏的恶劣。
第二次是在动物园的海洋馆见着他,那个黄昏有清风衬着,千里晚霞明,暮云重。他在海洋馆的表演区被黄金蟒缠进水里,到了医院又逞强,睡觉的时候格外粘人。
第三次是在通惠河边见着他,那个夜里星云缱绻。他躺在床上伸舌尖舔了嘴角,特诱惑,特撩人,欲望霎时扰乱心绪。他和他无比的近,唇齿相触,到最后气息不稳,胀得生疼。
第四次是在异国他乡的市集上,那个傍晚的海风一直在吹,有些喧嚣,有人来人往。他脖子上骑着一个黑人小孩,脸上蹭了冰淇淋。他躺在沙滩上讲他的小时候,后来踩了叫“鬼”
的海星,爬了棵底下是怀抱的树。
一次比一次相见艰难,一次比一次隔得时间长远。
他有时候特别近,有时候特别远。
梁义在月光下的身影有些落寞,他动作缓慢地拿出他:“在宾馆吗?”
等待这种事,一秒钟都算漫长。
舒倾浸在浴缸里仰着头,花洒的水源源不断浇下来。
熬不住没头没尾的等待,梁小雏儿怕极了他遇到什么危险,于是鼓起勇气打了电话过去。
漆黑的房间里终于有了微弱的光亮。
即便是在露台下面站着也能看到,却始终没人接听。
梁义心里有些慌,在听到第二次冰冷的机械回绝声后差点儿就上了台阶。正待挪步的时候忽然见了房间里的另一种光亮,是打火机或者火柴才能出的光亮。
一燃火苗着了又熄。
舒倾坐在床上,身上的水珠缓慢往下淌。他拿过手机翻了翻,看到三通未接。两个是梁义才打过来的,一个是梁正打过来的。
屋里终于开了灯。
梁义站在台阶下面看他,看他腰间围着浴巾,斜倚着桌子把手机拿到耳边。
电话接通了,他说了句什么,他在笑,他细微地勾着唇角。
可那通电话不是打给他的。
梁义垂下头,不知道自己刚才的悸动有多蠢。随后极苦涩地安慰自己,说,他没事就好,他好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不重要……吗?
真的连回一条消息都不屑于吗?
露台台阶下面落寞的身影离开了,走得缓慢,最终杳然无踪。
梁正才下飞机便想着打电话给舒倾,电话响了,没人接也没人拒接,就一直响着,声声催人,戳在心上。
大概是在外面没有听到吧,他这么想着,了条消息过去:“看见之后回电话给我。”
从下午一直等到夜里,接了很多电话,却唯独没有他的。打了很多电话,却唯独没联系上他。
梁正担心又有些着急,明天就要去一个几乎没有信号的地方了,想在这之前联系到他。就算随意说说什么,就算什么也不说,都好。
他又打了通电话,等了没多久,终于收到了回电。
“梁主任,深更半夜的,有何贵干?”
“没什么,”
梁正听到他不大正经的语气终于放下心来,看来他没大碍,看来他心情好的差不多了,于是说:“我看了你的稿子,写得不错。”
舒倾笑一声,当真不愿在他忙碌的时候还给添麻烦,“嗯,我改了好几次。”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夸你两句是吧?”
舒倾细微地勾着唇角:“夸我?你就只能干点儿那么虚的事儿?能不能来点儿实质性的东西?”
“既然你都开口了,那肯定没问题,”
梁正笑道:“等你回来。”
又是等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