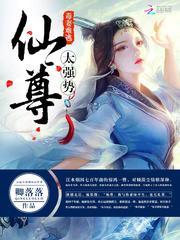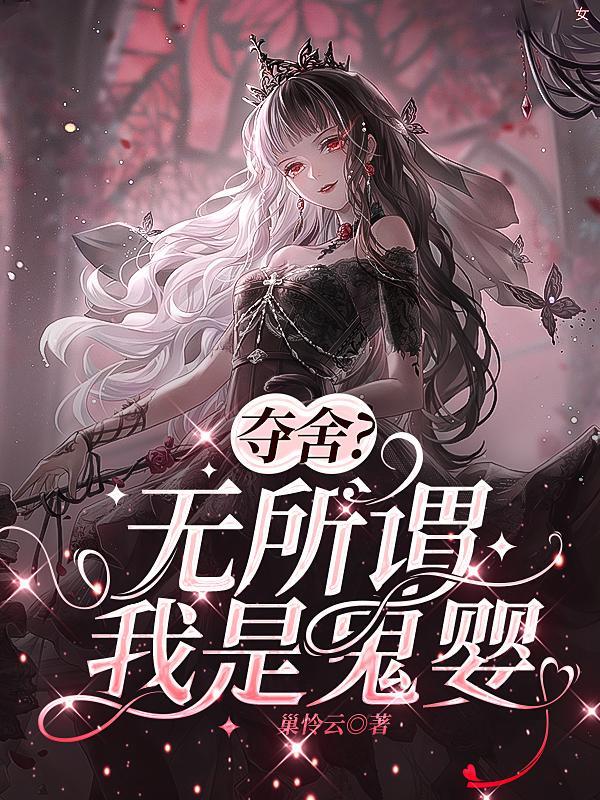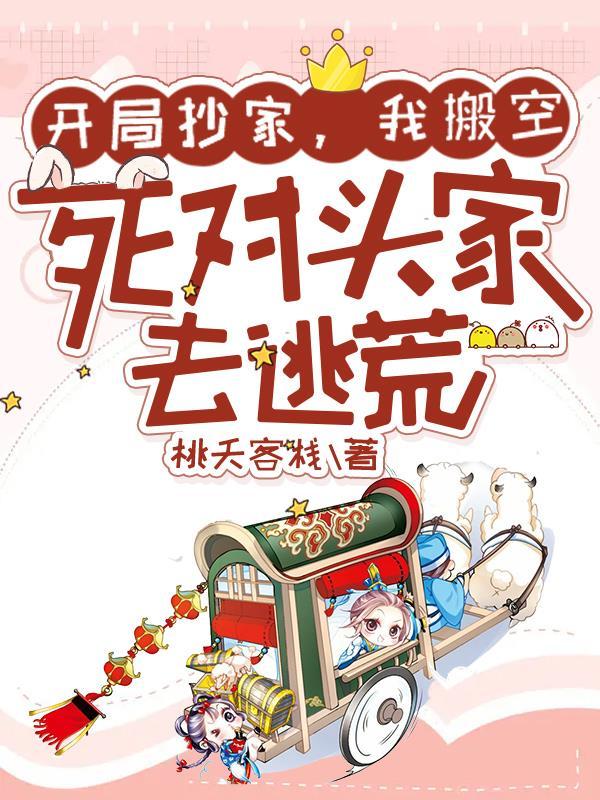69书吧>山河万里图 > 第44章 真相(第1页)
第44章 真相(第1页)
也不知道是因为前面哭累了,还是手刃了仇人之后心情平静了一些,杜阳虽然还是抽抽噎噎,虽然这个年纪的孩子逻辑性没有那么强,却到底算是口齿清晰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他说得断断续续,宇文曜和温谨言听得磕磕绊绊,尽管有些吃力,最后也总算是把前因后果理出了个大概来。
听完他所能想起来的所有事,宇文曜强压下满腔的愤懑,让人把杜阳带下去安顿好,等孩子离开,屋内的两人依然相对无言。
杜阳的话里只有一小部分的细节,却也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人面兽心的李县令为了某种理由将所有人聚集在广场上,在“赈灾”
的粥米里下毒,一举毒害了全县的百姓。
可再往深了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又是怎样等聚集所有人,他却并不知道。
仅仅如此,他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半大孩子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亲人、玩伴是什么感觉。
更可笑的是,他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山匪,亦或者是被引入至此的那些西洋兵。。。。。。
可结果呢?
没有外敌,不是山匪,这满城的百姓,居然是尽数死在自己的地方父母官手上。
宇文曜越想越觉得这事太匪夷所思。
到底是自己对于人性的认知太过乐观,还是大耀的现状实在太令人忧虑?
他的手放在桌上,攥着的茶杯已经无意识捏碎,直到瓷片扎进手心,他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疼。
温谨言听到声音也才回过神似的,重重叹了口郁气,把烛光拿近了一些,沉默着抓过他的手,用桌上烧开已经冷却的水清了一遍血迹,烧热了匕后一片片把瓷片挑出,撒上金疮药,才一边包扎,一边开口“杜阳说得还是太含糊了,他只是个孩子,经历了这么大的事,遭受了打击,恐怕记得的也不多,不过关键信息已经有了,足够作为引子。”
宇文曜知道他的意思,点了点头“你去问吧。”
温谨言替他包扎好,托着他的手小心放回桌面,轻声应道“好。”
他说完起身要走,却被宇文曜拉住了,一回头,就看那人垂着眼,烛光打在他眼睫上,在他原本深邃的眼下打上了一片阴影,显得这平日里不是纨绔便是张扬的男人看起来莫名地疲惫,心里一角的柔软被无意勾起,温谨言连说话的语气都柔和了一些“怎么了?”
宇文曜按了按眉心,撑了下桌子起身“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温谨言想劝,张了张嘴,到底是改了口“好。”
李家的遗孀中有一妾室原本是土生土长的闵梁人,那些死去的百姓里有她的家人,从小玩到大的小,心里早埋了巨大的愧疚,于是温谨言刚一说出“李县令已经死了”
,以及“我们有证人指证就是他毒害了全县上下几千口人”
这两条定论后,口子便轻易被撬开了。
年关之后,大雪淹没了整个山区。
上山的路都被大雪封了,水面也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靠山吃山的百姓们无法可想,家家户户只能把家里所有能吃的都拿出来,抠抠巴巴地指着这些屯粮勉强度日。
后来一个月两个月地过,大家都觉得再这么下去长久不了,再看看一开始还有人找县令求助,可是过了这么久都没见有动静,便更觉得心寒了。
有胆子大的闹到县衙,李县令就说朝廷拨付下来的钱粮在半路被山匪劫了去了,已经在上报朝廷,还要大家再等等。
但年轻体壮的人等得住,体弱的老人孩子却都等不住了,眼看着县令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敷衍他们,终于有人等不了了,就提出来去大伙结伴去邻县寻求帮助,就算真的遇上了山匪,也比在这里活活饿死来的强。
可是七八天过去了,出去的人一个都没回来。
后来李县令把那些人的尸体送回了各自的家里,说是这些人出城的时候被山匪在半路杀害了。
这事一出,百姓的心更慌了,可在他们眼里,毫无作为的李县令却变成了一个好人。
这些老百姓哪里能想得到这种人面兽心的家伙在背地里都干了什么好事?他们只知道如果不是这位李县令,他们的家里人都要曝尸荒野无人收尸。
可心里感恩是一回事,该饿肚子的时候,还是会饿。县城边上能刨的树根都刨干净了,朝廷的拨付的东西还是没到。
只不过这回再也没人觉得是李县令的责任了,所有人都在骂山匪,有人提议大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想活着,就要去剿匪,于是挑了一个读过书的人,给大家制定了一个计划,然后这人就带着这个计划连夜去敲李县令家的门。
结果这一去,事情就一不可收拾了。
李县令家的院墙很高。
只可惜再高的墙,也有透风的一天。
那人斗志昂扬地出去,骂骂咧咧地回来,告诉所有人,李县令在骗大家,那狗官私吞了朝廷拨付钱粮,还勾结了山匪,就为了不让消息走漏出去,营造出闵梁县的灾情已经平复的假象。
这事是什么程度?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那几个被李县令带回了家里人尸体的人先跳出来说不信,说要当场找李县令对质。
消息一夜之间传得满城风雨,第二天天没亮,大家伙就聚集在县衙门口,等着李县令开门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然后那李县令道貌岸然地说了一堆慷慨陈词,说自己绝没有私心,说钱粮昨夜刚到,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赈灾工作,最晚未时就会在广场上给大家伙施粥,但是因为考虑到闵梁县很多年没有遇到这种灾情,他们也不确定拨下来的粮食够不够分,所以未时之前必须所有人都要到场做在册记录,后面会按照登记的情况给家家户户的人口分粮食。
这话一出,还有哪户人家会缺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