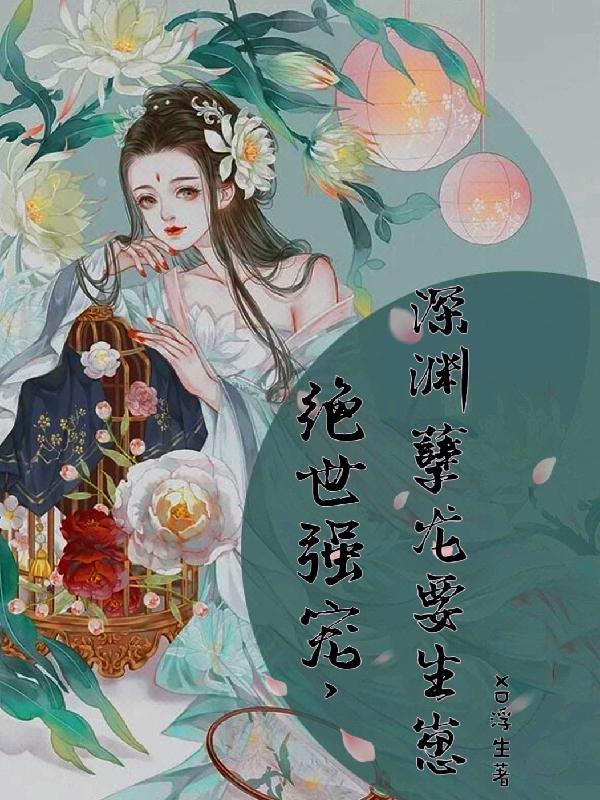69书吧>梁园编剧 > 第六章 金针术(第1页)
第六章 金针术(第1页)
小楼一走进院子,见到的就是一地狼藉。
碎成无数片的琉璃瓷片,有的润白如玉,有的晶莹剔透,显见都是待客用的不菲之物。
一位身长玉立的白衣公子,负手而立:“张公子今日喝多了,送客罢!”
那名唤张公子的蓝袍劲装男子一脸尴尬,收回了手中刚舞完的剑,看向白衣公子,竟是有些讪讪:“温兄,我绝无旁的意思,你莫要多想……”
白衣公子语气平静:“送客。”
显见平日里他积威甚重,满院子人无一敢大声吭气,只能目送那名蓝袍张公子一脸挫败地走出院子。
院门口候着的小厮低声对张公子陪着不是,又道:“我们二爷已经备下了酒菜,想请您赏光小酌一盅呢。大公子许是累了,想歇息呢。”
这才听见那张公子一挥袍服,大步流星地走了。
小楼脚步声极轻,见那张公子走远,索性对着白衣公子朗声道:“河东梁氏梁小楼,按温二公子嘱咐,特来拜访大公子。”
只见那白衣公子闻言缓缓转过身来,他身形利索,步履无声,看着颇为健硕,显见是个练家子,只不过眼睛绑了一条白色的长锦缎,遮住了目力。
“东官跟我提起过你,这小子整天不学好,现在连未及笄的小娘子也撩玩起来了?”
白衣公子神情语气较之温夫人更为倨傲轻蔑,小楼与之隔着三步远,已经感受到一身威压。
梁小楼也不恼,她心知温家人都是一副样子,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实力不给好脸。
“大公子肯拨冗相见,想来是抽空听了小楼的那诗吧。”
梁小楼努力在面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这样说话的声音也会悦耳一些。
白衣公子并不想轻易放过:“如你所见,我的眼疾,东官跟你提过吧。”
梁小楼轻声道:“未曾,二公子只说,大公子深居简出,轻易不见客。”
“哦?”
白衣公子仍是语气轻佻,“那‘云开见月明’,何解呀小娘子?”
梁小楼见他虽然语气轻慢,行止之间却颇为沉稳,心下有数,朗声道:“大公子少有才名,总角之年,就有佳作传世‘满目河山远,大漠狼烟直’,后来却沉寂了。小楼这次有幸来访温府,眼见府中路上并无软轿或素舆的齿痕,想来能将大公子困于院中的,不是足力,而是目力了。”
“嗯,有几分歪理,”
白衣公子右手拂了拂肩上的落叶,“院里有些乱,你随我来堂内品茶吧。”
堂内分宾主坐定,小楼悄无声息地四下打量:这大公子温东相的屋子,处处透着冷肃之气,就连屋内几案上摆着的花瓶,都是白瓷底配山水墨画图,一丝彩色也无,哪像温东官,养只鹦鹉用的还是掐金丝珐琅彩的笼子。
温东相坐听梁小楼放下茶盏,便开口:“我这眼疾,已经延请十几位名医看过,除了太医,前朝御医也是有的。你一个幼女,若是有什么难处大可跟我母亲开口,左不过一些后宅妇人之事。便是有几分祖传偏方,也不过是治治体胖脑热罢了。今日我应了东官的面子放你来,不过是见他许久没有事情求上我这个哥哥,若是无事,你喝完茶可以去。”
两三句话,已经将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语气清淡平和,平湖无波一般,毫无情绪。
倘若梁小楼是个假咋呼的小姑娘,到了此处,确实该见好就收。
可她两世为人,所见所学,即便是温东相这样大族嫡子,也未必能及。
想到这里,小楼自信地挺了挺平如桌板的小胸脯:“寻常名医治疗眼疾,无非三个法子,内服,外敷,针灸。大公子,此前可是试过这几种方法?”
……
想到这里,小楼自信地挺了挺平如桌板的小胸脯:“寻常名医治疗眼疾,无非三个法子,内服,外敷,针灸。大公子,此前可是试过这几种方法?”
温东相颔不语。
梁小楼沉声道:“小楼斗胆,请公子卸下布条,让小楼诊治。”
温东相沉默了一会,仿佛想透过那层锦缎看透这个年少气壮的小女子:“东官同我提过,梁家想把你送入我们温府?”
小楼笑应:“如果小楼为公子治好眼疾,便是温府的恩人,如果小楼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伺候人,那便是温府的奴婢。大公子,若你能选,是乐意自在为人,还是愿意屈身为婢?”
“好一个自在为人!”
温东相似有所感,“我已经不自在数载,也罢,姑且再信你一次。”
说罢他似乎想起什么,语气变得狠戾:“今日之事,你不可外传,倘若泄露一二,小小梁府,就不必存于汴安城了!”
梁小楼也不接话,转头望向屋内的侍从:“我要一盆冰水,一碗烈酒,几只暖香,十块洁净未用过的丝绢,三枚带手柄的铜镜,还有一架可调高低的烛灯,再将这门关上,室内所有窗子都遮上,为大公子看诊需弱光。”
然后她起身向前两步,径直站到温东相面前:“小楼已经交代好了,还请大公子,自行卸甲。”
温东相闻言身子微微一震,一时间内心百感交集。
他自幼身负温氏一族的厚望,不但文采出众,武功也不弱与一众勋贵,年少轻狂之时,也曾属意弃从戎、大漠狂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