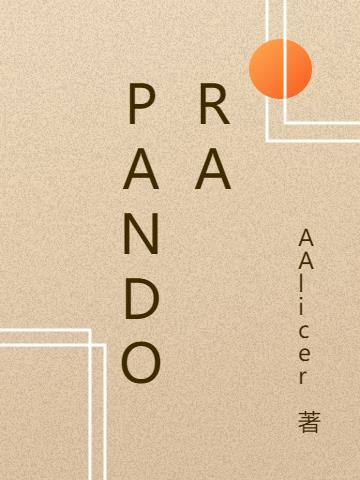69书吧>情人关系怎么相处才能长久 > 第59页(第2页)
第59页(第2页)
半天王西夏回她:明天面聊。
第二天也没面聊,王西夏一早就坐了徐清河的车回北京。庄洁坐在屋檐下晒太阳,第一回感到了孤独,也感到了被抛弃。从王西夏和徐清河谈对像后,王西夏联系她的次数日益减少。
这整整一年,庄洁基本每天都微信同她聊天,长则两小时,短则几分钟。自从陈正东跳烟囱后,她就担心王西夏想不开,每天每天地陪她聊。
她忧伤着忧伤着就开始困,坐在竹椅上打瞌睡。何袅袅蹑手蹑脚地过来,朝她身边一蹦,“姐!”
庄洁吓得拿鞋子掷她,她做个鬼脸说:“姐,你谈个对象吧。我看你自己坐这好可怜,等你八九十岁……”
“滚蛋啊。”
庄洁打个哈欠问:“咱妈呢。”
“去找大师算命了。”
“算命?”
庄洁被太阳晒觑着眼。
“她和邬姨一块。”
“闲得慌。”
庄洁伸个懒腰,冬天的太阳太舒服了。回屋拿了个零嘴,骑着电瓶车去烧鸡店。
路上遇见陈麦冬,她扭头就走。
“犯得着?”
陈麦冬拦住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点度量都没。”
……
庄洁哑口无言。
他把她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接着又了无诚意地道歉,“姐儿,对不住啊。”
庄洁骂:“我……”
“我、日、你。”
陈麦冬动口型。
……
“咱俩比着爆粗,看谁爆得更粗。”
陈麦冬看她,“老子治不了你。”
……
庄洁回了烧鸡店,店里阿姨告诉她,今儿一早就有人送了箱车厘子来。她问是谁,阿姨随口就说:“殡仪馆里给死人化妆的那个男人。”
庄洁被“给死人化妆的男人”
这个称号刺到了,她看着阿姨,想告诉她应该用尊重,至少礼貌的语气说。但阿姨完全不自知,一面腌着鸡排,一面用喜庆地口吻说她闺女怀孕了,医院也检查了,是个大胖小子。
算了,她想。
蹲下拆车厘子箱子,那边阿姨搭话,说车厘子可贵了,上个月她女儿去市里检查,市里随手捡了几颗一上称,乖乖,小五十块。
庄洁让她装点回去,她不好意思地摆手,说吃了也到不了哪。庄洁给她装了点,又给店里的员工洗了盘,剩下的拿回了家。
傍晚寥涛同她闲聊,说今天去算命了,那瞎子太神了,说的十件事里八件都准。
庄洁问:“你算了啥?”
“我啥都算,算了你们姊妹仨。”
寥涛说:“我算袅袅能不能考市里,他说没戏。”
“他直接说没戏?这算命的也太干脆了。”
庄洁说。
“他不整文绉绉那一套,也不含含糊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还给了你的生辰八字,他说不急,说你明年就能成事。”
……
“你有个喜欢了四五年的男人?”
寥涛看她。
“谁说的?”
“这瞎子说的。”
“厉害!”
庄洁吃惊。
“你还有这事?”
寥涛咬着车厘子套她话,“你公司里的领导?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