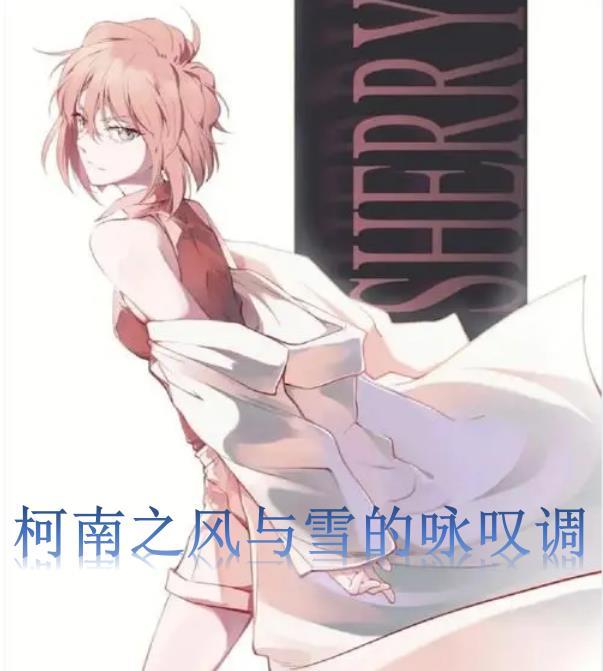69书吧>如岳临渊的寓意 > 第36页(第1页)
第36页(第1页)
罢了,这样安详的时候不多,能偷得一刻是一刻。
寅卯之交刚过,石室外传来东厂侍卫的禀报,楚岳峙在司渊渟怀里醒来,初醒时他还有些茫然,对上司渊渟清明的眼眸才渐渐清醒过来。
他被司渊渟抱着坐起,中衣松垮领口半开,露出锁骨那一大片肌肤也不自知。
司渊渟眸色深黯,看着他锁骨上那一道斜长的深紫色刀疤,问道:“这伤怎么来的?”
楚岳峙不知他为何突然问及此事,他身上深深浅浅的伤疤不少,锁骨上的这道伤是最为凶险的一次,拖了将近一个多月才有痊愈之势,他当时在营帐里躺了十多日不能下地,军医更是深恐保不住他的命自己的项上人头也会跟着不保,日日诚惶诚恐地给他医治,他浑浑噩噩地在鬼门关前挣扎着,好几次一只脚都已踏进了棺材里,却又被梦里少年一声声的“楚七”
给唤了回来。
这伤太深,这么多年他身上其他的伤疤都渐渐淡去褪白,唯独锁骨上这道依旧不见好。
“出征第二年,我灭那鞑靼时,被一个据说曾作为使臣出使大蘅国的卑鄙之徒偷袭砍伤的,但我也亲自将他手脚都斩断了,再用大蘅国的旗杆插着他的残躯示众,让他失血暴晒至死。”
楚岳峙想起那人的面孔,面露憎恨,“那人面目狰狞生性残暴,不仅杀了我不少将士,还曾抓过不少大蘅国的子民用残忍的手段折磨,我只恨自己出征太晚,让他嚣张至极的肆虐多年。”
揽在楚岳峙腰上的手臂收紧,司渊渟听完楚岳峙的话后低头将唇印在那伤疤上,一言不地细细吮吻过伤疤的每一寸。
“嗯……司渊渟,不要又……”
楚岳峙偏过头,突如其来的亲密行为让他下意识想要躲避逃离,可司渊渟的唇是那样的温软,像在亲吻什么宝物般充满怜爱,他抗拒的念头刚起,伤疤上传来的酥麻感便让他软了手脚,他的身体迅背叛了他的意志,如他说过的那般对司渊渟臣服,他咬紧下唇不让低吟泄漏,整个人都无力地偎依进司渊渟的怀里。
司渊渟吻过他的伤疤又在他肩颈处流连,留下好几个鲜艳欲滴的印记后,才在他耳边说道:“起来去见见那林芷霏与江晟。”
将头从司渊渟肩上抬起,楚岳峙颤着手拉起衣领,又用手捂住颈间被司渊渟吻过的地方,眼尾通红的桃花眼流露出一点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无措。昨夜之前司渊渟都不曾吻过他,也没吻过他身上其他地方,一直以来都是用手或器具玩弄,如今他让司渊渟抱着共眠,醒来又以这缱绻的姿态与他亲密,他却竟也没有多少抗拒,难不成他才与司渊渟往来几个月就已经不知廉耻地堕落了吗?
难以接受地想要推开司渊渟,可直起身后还没来得及有更多动作,司渊渟已随手替他理好歇息过后散乱的墨,动作自然顺手得仿佛早已做过无数次那般,他失神地看着司渊渟放开他后径自下榻去换上官服,心中自厌自弃之情比过往任何一次都要更为沉重。
第21章先礼后兵
离开石室前,司渊渟侧看已恢复平常那端雅清冷中带几分慵懒模样的楚岳峙,淡淡地说道:“出了这石室,本督怕是不能轻易让安亲王离开东厂。”
楚岳峙眉目不动,道:“此事闹得这么大,皇兄若不让本王这个臣弟受点苦,心里那口气也消不下去,督主如需用刑,本王也受得住。”
“想多了,本督手中的权势可尚未到能对安亲王动刑此等嚣张的地步。”
打开石门,司渊渟侧身让道,再开口已是熟悉的太监腔调:“安亲王,请往这边走。”
兜兜转转地穿过昏暗的走道,司渊渟领着楚岳峙来到审讯室,林芷霏与江晟被分开关在两间审讯室里,满脸疲色的他们显然皆是一夜未眠,并且除了他们面前的那根蜡烛,审讯室里皆是一片黑暗。
“安亲王可要想清楚是否有要向本督交待的事,否则只怕是要如他们一般,在这审讯室里好生待上几个时辰了。”
司渊渟说话间,一名东厂侍卫拉开另一间审讯室的门,里面黑漆漆一片,却是连一根蜡烛也没有了。
尖利的太监腔调在这昏暗的空间里显得异样诡异,可楚岳峙听了也只是轻轻一笑,道:“本王要交待什么呢?这里面的两人,本王都没见过,督主拿他们吓唬本王,不知意欲何为。”
“当真没见过么?”
司渊渟状似无意地扫一眼那拉开审讯室门的侍卫,冷笑道:“这女子可是方知礼的妻,安亲王该不会认不出来吧?”
惊讶地抬眼看司渊渟,楚岳峙又认真往林芷霏所在的审讯室里瞧了两眼,摇头道:“方知礼的妻本王为何要认得?督主可曾见过有哪个男子去寻欢作乐会把妻带上?”
“本督也只是依例问询,安亲王何必急着讽刺本督是个不懂男子之乐的阉人?”
缓缓转动拇指上的白玉扳指,司渊渟又道:“安亲王既说不识方知礼的妻,那这间审讯室里的这位,安亲王总不会也说没见过吧?”
楚岳峙依着司渊渟的话朝江晟的审讯室门口格子望进去,仔细瞧了许久后,又是一脸无辜地说道:“督主快别为难本王了,这人是何方神圣,本王当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此人乃礼部主司江晟,朝廷官员,安亲王竟也说没见过?”
司渊渟毫不掩饰话中讥讽,“虽说我朝六品以上的官员才需日日早朝,可安亲王别忘了,凡京朝在职官员都可以上朝奏事。这江晟,之前可上过不止一次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