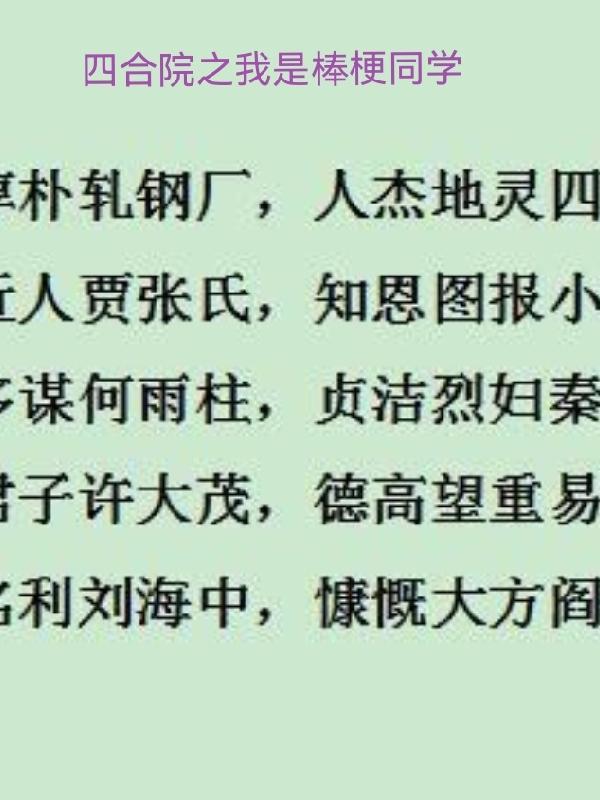69书吧>嫁给暴君和亲钱十冠 > 第53节(第1页)
第53节(第1页)
“怎么样?”
他眉心聚了散,散了聚。诊了良久,景仲终是不耐,开口问道。
“前日诊脉,王后脉象都比今日平稳。这两日王后是否又受了寒?”
虞碌纳闷。
景仲偏过头望向画溪。
画溪摇头:“没有,我都是听先生吩咐,这两日门都不敢出。”
顿了顿,她又补了句,说:“我身子骨一向不好,是小时候吃了的亏,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虞碌正要点头,眼睛对上景仲的双眼,他直勾勾地看着他,信手端了桌案上的茶盏,只问:“能治好吗?”
虞碌顿觉头上悬了把剑,他道:“既是早年吃的亏,那就不是一朝一夕能调理好的,假以时日……”
“孤是问你,在去往信城之前能治好她吗?”
“臣定竭尽全力。”
“能治好吗?”
景仲语气里含了几分隐隐的不耐烦。
画溪心里咯噔一声。她生怕景仲一个不高兴真的把虞碌给宰了,犹豫了下,起身向景仲走去:“麻烦虞碌先生了,请你现在去帮我开方子吧。”
虞碌如蒙大赦,匆匆告退了。
殿里只剩他们两个人。
画溪看着景仲坐着的身影,心里颇有几分挣扎。
从她踏上前往柔丹的马车那一刻起,她就知道自己的命由不得自己做主。
现在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做主一回了。
千算万算,算错了人心。
原来她也会因为景仲纠结。
平心而论,景仲待她已经算是厚道。不管这厚道是因为什么,至少他真真正正护过自己。
时至今日,她对景仲怕过、怨过,到现在,也感激过。
尤其是近来她生病,景仲看得极为重要,虞碌大夫都喊了好几回了。
照理,她就算死在王宫,也该留在景仲身边尽忠的。
但她低估了人的求生欲。
她想起宫檐下挂着的那些人皮灯笼,心又硬了起来。
“王上。”
她蹲下身子,像只温顺的猫儿一样伏在景仲的膝上,乖巧得不像话。
“是我不中用,总是让王上担心。”
声音也柔得像一汪水。
景仲垂眼看她,说:“哦,你哪只眼睛看到孤担心了?”
画溪被噎了一下,神情有些尴尬。
是哦,景仲要担心也是为大邯公主担心,可不是为了她。
“李蛮蛮。”
景仲看着画溪的眼睛,视线逐渐下移,指腹揉了揉她的鼻尖,嗤笑了声。
画溪仰着脸,乖顺地“嗯”
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