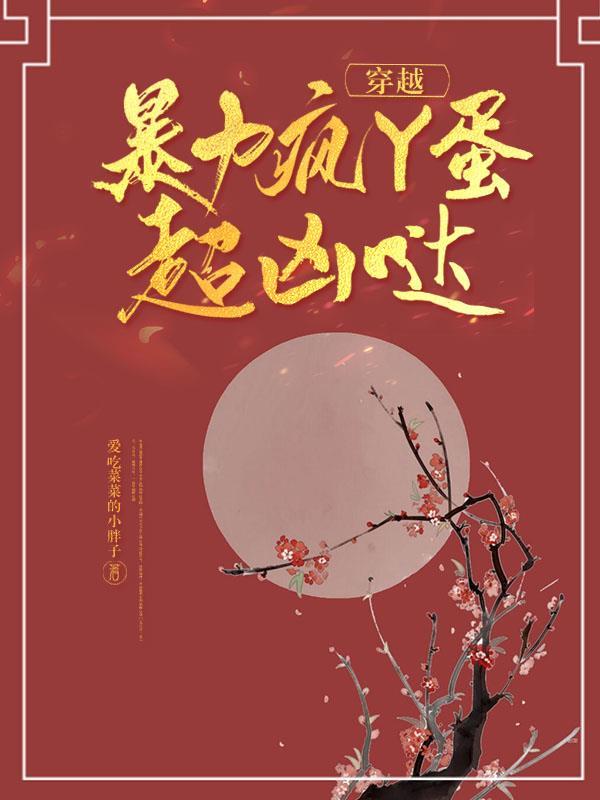69书吧>好困的英文 > 第16頁(第2页)
第16頁(第2页)
但她僅是意外,並不覺得惶恐,畢竟那一間臥室並非某個人的固定房間,留言或許是林氤為了叮囑其他人所寫的。
七年後的靳搖枝看不到樓上種種,不得已跟著林氤搬桌堆椅,把那裂開的窗稍稍擋住了。
她聽見樓上傳來聲音。
「譜子是你畫的?」
25
在一地狼藉中,林氤仰頭說「是」,她沒有拂開手上的灰,而是拿了掃把,隨意將地上零碎的玻璃掃作一團。
堆起的桌椅並不能完全將風口擋住,所以林氤掃得毫不用心,只為避免大塊玻璃將人扎著。
伴著玻璃的嘩嘩聲,林氤又說:「裡面有幾是我和寧橙一起寫的,你要聽聽嗎。」
靳搖枝就伏在欄杆上,後背一個勁冒著寒意,但這寒意的來由和林氤無關,只是因為走道太長,也太暗。
她翻開曲譜,如今的光線大約還能看清譜上的內容,但她對音樂一竅不通,譜子是看不明白的,只依稀能懂得歌詞的大意。
不得不說,這詞和林氤本人毫不搭調,有幾分像中學時候備受詬病的意識流作文,一些辭藻華而不實,通篇看下來就是毫無中心的無病呻吟。
「詞也是你寫的?」靳搖枝看得吃驚,在她看來,林氤的內里不該是這樣的。
「譜子是我編的,詞是寧橙寫的,她執意要親自作詞,在終稿之後,再由我抄到曲譜上。」林氤放下掃把,洗乾淨手才將事前擦乾淨的吉他拿上。
「字寫得不錯。」靳搖枝一頓,又繼續評價:「詞不太好懂。」
「不用給她留面子。」林氤說得平靜又淡然,「她中學時候就是這樣,喜歡和應試作文對著幹,骨子裡帶著點文藝病。」
「總得要有點自己喜歡做的事。」靳搖枝委婉地說,「看來你們認識很久了。」
「發小。」林氤說得簡單,她拎著吉他邁過那一堆破碎品往樓上走,迎上了靳搖枝的目光,「說起來,三年前會去看你的展,其實是應了她的邀。」
靳搖枝微愣,詫異地問:「那她又是怎麼想到要去看我的展。」
「那次我們恰好在J國旅遊,從長輩的手裡拿到了邀請函。」林氤接過靳搖枝手裡的曲譜,又說:「那張邀請函設計得很好看,寧橙對好看的,總是沒有抵抗力。」
「那你呢。」靳搖枝問得不清不楚,使得咬字也變得黏黏糊糊。
她還是主動的,隨時隨地都想占據主導位。
林氤看著靳搖枝說:「我也是。」
隔著林氤的身體,七年後的靳搖枝又得以與自己對視。
來自七年後的靳搖枝很難形容這一瞬的離奇,離奇就離奇在,她不明白「自己」的神色為什麼會帶著探究。
是不信林氤這番說辭,還是其他?
![女道君[古穿今]](/img/14951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