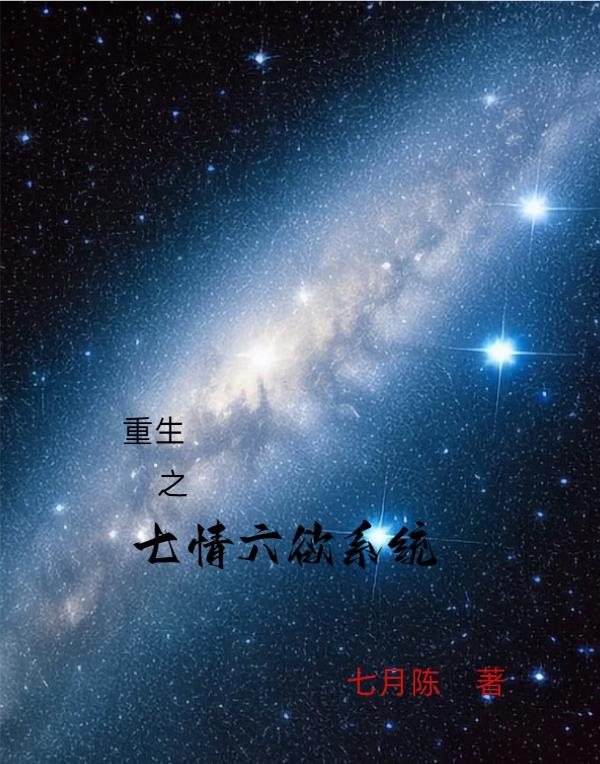69书吧>风起风起 > 第163章(第2页)
第163章(第2页)
温南晚扯了扯嘴角,眼里的心疼更盛。
她看着马上就要站起身去拿的人,先一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去拿。”
她随手拿了瓶就朝画架前的人走去,眼睛点了点他的腿,“你不应该换个姿势吗?”
谢之寻身子绷了一瞬,接着那条撑着的腿屈膝跪下。
双膝。
绝对臣服的姿态。
温南晚坐到椅子上,抬手捏起他的下巴,“张嘴。”
他乖乖照做。
瓶口碰上他的嘴唇。
他微仰着头迎合,纤细冷白的脖颈隐隐凸起青筋。
完完全全在配合她“玩。”
温南晚最终没抬起来手。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泪水也再一次止不住滴落,声音哽咽,“谢之寻,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是好?”
面对她突然喊停,他眼里有迷茫困惑可偏偏没有一丝一毫对她想法改变来改变去的不耐烦。
“怎么了?”
“怎么了?你酒精过敏也要陪我玩是吗?”
她声音提高,手里的酒瓶掉落在地,随着一声清脆的玻璃声响,她的质问又一次响起,“拿命玩吗?”
无论她做了什么,他都是“好”
要他的命,他也好。
“在小姐走后,老板有时候会一个人去画室喝酒,他酒精过敏,喝的少了,就是身上起红疹,吃些药就缓过来了,可是有几次,他喝到濒死。”
听到女孩说这些的时候,她心快痛死了。
比刀划在手臂上还要痛。
密密麻麻的疼痛侵蚀着她的心脏,自责心疼的情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如果她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真的把那段记忆瞒她一辈子吗?
谢之寻看着泪流不止的人,站起身去帮她擦眼泪,“只要你想,我能,就好。”
只要你想,我能,就好。
温南晚再也忍不住,环住他的腰,失声痛哭起来。
谢之寻柔声去哄,但是没用。
无论他怎么哄,人就是搂着他哭。
眼看哭的要岔气,他把她从自己身上拉了来。
一只手箍着她的肩膀,一只手帮忙擦泪。
“不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