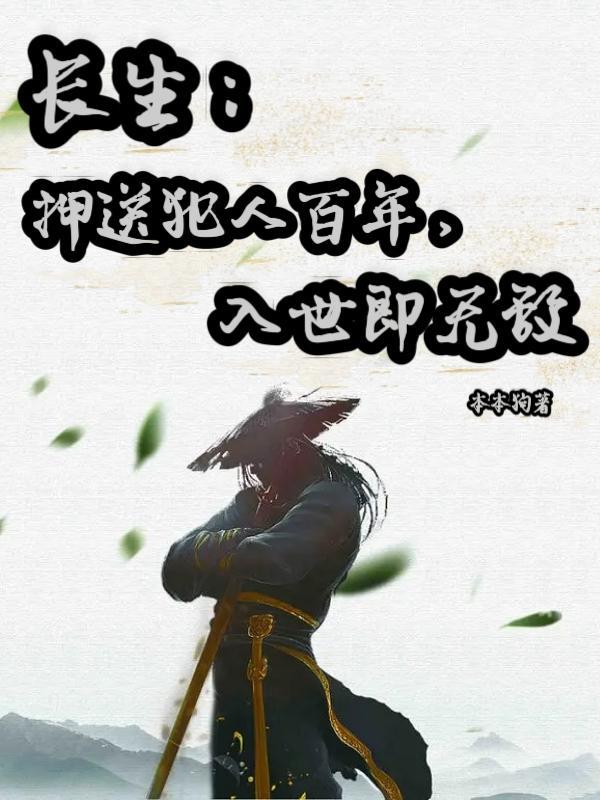69书吧>上船暴富但下不了船在线阅读 > 第39节(第2页)
第39节(第2页)
在这十五分钟里,白昼混入了和她差不多年纪、差不多打扮的学生中。
同茂的发布会在A大掀起一股仿生机械文化热潮,就连她为隐藏身份而戴上的半边涂鸦金属面具,也成了并不罕见的饰品。
像所有普通的A大学生一样,白昼穿过正在开展社团活动的广场,途经刚下课的教学楼,走完了林荫遮蔽的大道。
她和无数人擦肩而过,中途因为撞到别人而道歉,而对方只会摆摆手说,同学,你的面具很酷,然后她们彼此相视一笑,各自消失在人潮中。
下午时分,阳光金灿灿地落下来,她双眼里的摄像元件捕捉到的一切都因为过曝显得梦幻无比。
她最后停在某个监控的死角。
楚来托着腮,已经听入了神,半晌才接话:“乌冬在那里等你吗?”
白昼摇头:“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他的面具。我们左右隔着一段距离,一起走到了那里。”
她重新去看那张照片,指尖落在上面,像是想触碰乌冬伸出的手。
拍立得相机在这个时代仍旧有一定受众,A大不缺有钱有闲,喜欢摄影的同学,白昼找路过的人借到相机,给自己和乌冬留下了两张照片。
那短短的十五分钟不够白昼告诉乌冬自己的身世,也或许是她还留着一份私心,希望自己真的只是A大里最普通的一员,午后从课堂中出来,在校园里闲逛,和自己心爱的人约会,拍下纪念的照片。
白昼的脸习惯了设定好弧度的笑容,而当面对镜头的时候,她想以白昼这个身份露出真心的微笑,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表情中的僵硬。
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乌冬拿着她的照片看了很久,说她笑起来很好看。
“乌冬的那张照片被我藏在了墙角的砖缝下,拜托李研究员帮我带回去。因为很快,父亲就找到了我。”
接下来的发展简直是直转急下,明明还是一样亮着昏黄壁灯的房间,白昼却像在用最平静的声音说一个惊悚故事。
“回去以后,父亲推掉所有的工作在造景棚里住了一周。每天醒来时,他都在我的房间门口。”
至于为什么白昼一直待在房间里,是因为丁寻理把她的腿给卸掉了。
丁寻理很悲痛,他花了近二十年研发的心血,人类文明伟大的结晶,却不愿待在他苦心孤诣营造的乌托邦里。
白昼是他最珍贵的理想安放寄托的载体,丁寻理不是女人,没有孕育的能力,只有看到白昼时,他才有了自己曾亲手塑造出一个人的实感,并在这其中感受到自豪。
可令他自豪无比的女儿,却用一场闹剧狠狠羞辱了他的信任。
那七天里,白昼每次从休眠状态中醒来,都能看到丁寻理坐在门口望着她。
有时叹气,有时落泪。
“父亲告诉我,当看到我失去双腿的样子时,他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还难过,因为他是人类,他甚至无法靠切断电源来阻止情绪的产生。”
楚来的嗤笑打断了白昼对那段昏暗日子的回忆。
“嘴上说说多没意思,他怎么不给自己的腿也来两刀。”
白昼侧头看她,楚来直视回去:“反正同茂是搞仿生机械的,他想装随时能装最新款。”
她没和楚来吵,只是摇摇头,匆匆讲完这段故事里并不愉快的结尾。
那七天像一场漫长的抗衡。
白昼是仿生人,只要有充足的电量,就能维持机能状态的正常。
但丁寻理不行,白昼望着他一点点消瘦下去,面颊凹陷,眼睛泛红,嘴唇失去血色,却仍旧雷打不动地在门口望着她。
他或许是想效仿自己最崇拜的古代哲人,耗尽生命枯坐,只为解开一道终极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