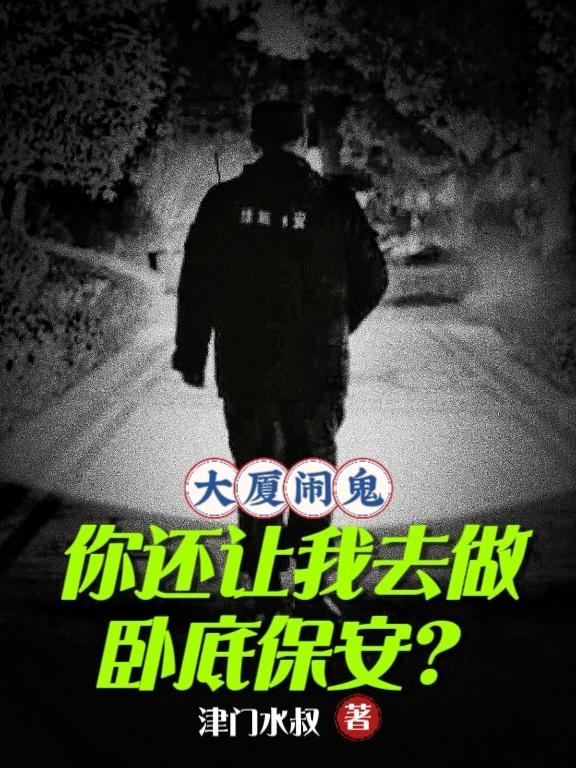69书吧>扫黑风暴原型 > 第57章 直捣老窝(第2页)
第57章 直捣老窝(第2页)
玻璃击碎了,没打到人。
吉普车疾而至,我纵身一跃,扑向北侧的玉米地,靠浓密的玉米秸秆遮掩自己。
吉普车在玉米地里旋转,大灯照着,轧向我的身躯。
我连滚带爬,不停地躲闪,大片大片的玉米秸秆被轧倒,他们像赶鸭子一样紧紧逼着我,不弄死我,决不罢休。
我身上刚刚愈合的刀口,全撑开了,二次开裂是最疼的,一种扒皮抽筋的感觉。
我不停地往北奔跑,用尽全力,蛇行走位,吉普车虽快,但它得拐弯,我不停地转弯,它一时轧不到我。
蓦地,我听到一声枪响,“嘭”
地一声,一团铁沙子向我袭来,他们还有一杆枪!
厚厚的玉米秸秆救了我,一阵噼啪作响,铁沙子穿过玉米秸秆,卸下了一部分的冲击力,几粒铁沙子击中我的小腿肚子。
人中枪之后,先感觉到的不是疼,而是麻,像是被什么叮了一下,而后才是疼,钻心地疼。
我生怕自己骨头断了,使劲儿蹬了蹬腿,没事,我还能跑,没伤到骨头。
只是小腿一阵热,是热血在流淌。
此刻,远处的国道上灯柱射来,警笛大作,喧嚣震天。
救兵终于来了。
我一瘸一拐,拼尽全力跑上国道,挥手呐喊。
吉普车调头就跑,关了车灯,蹿向西方小路。
我双手握枪,瞄准吉普车轮胎射击,可雨太大了,根本看不清,一枪打过去,没有击中。
我深吸一口气,赶快跑向孟威那辆桑塔纳跟前,探头一看,大惊失色:梦蝶呢?
我怀疑自己眼花了,使劲儿眨了眨眼,一伸手将车门拉开,弯腰进去仔细看,又摸了摸,后座上空空:梦蝶不见了!
孟威还在,歪着脑袋昏迷在驾驶位。
我的脑袋“嗡”
地一声:我的老婆啊!
我刚才只顾着和对方激战,对方肯定兵分两路,一路开着吉普追杀我,另一路用另一辆吉普车把梦蝶劫走了!
他们可是有两辆吉普车啊!
哎哟!可坏了!可坏了!
我捶胸顿足,恨不得杀了自己!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恐惧,把心爱的人弄丢了!
她落在了侯杰的手里!落在了魔鬼一般的人手里!
我心疼得无法呼吸:许小山啊,许小山,你这次是真的完蛋了!碎尸万段,也无法救赎啊!
两辆警车,三辆警用摩托,呼啸而来。
远远地一个声音大喊:“小山!小山!我们来了!”
我听出了是魏勇军的声音。
他们停下警车和摩托车,快步跑过来,魏勇军跑在最前面:“怎么样,没事吧?”
我指了指桑塔纳汽车,道:“赶快打12o,车上一位同事受了重伤,你们不要动他,他颈椎受伤了,等医生来!”
魏勇军点点头:“好!”
随即看了看汽车内部,“梦蝶呢?”
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漠然无语,心已经冷了,冷了,就会变硬,变得像钢铁一般!
我转身就走。
魏勇军一惊:“你去哪儿?”
我跨上一辆警用摩托,一拧钥匙,脚下一蹬,掉转车头,直奔西方小路追去。
那些年,因为“路面硬化”
政策实施,很多地方的土路都铺成了砖道,虽然不如柏油马路平顺,但比土路好多了,至少下雨不会陷进去。
我骑着摩托在砖道上飞奔,雨水打在脸上,冷风嗖嗖刮过,一身刀伤开裂,腿肚子上流着血,我却全然感觉不到痛,心里只有梦蝶。
追了六七里地,也不见吉普车的踪影,雨太大,实在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
况且我追的是第二辆吉普车,第一辆什么时候跑的,跑向那个方向,我根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