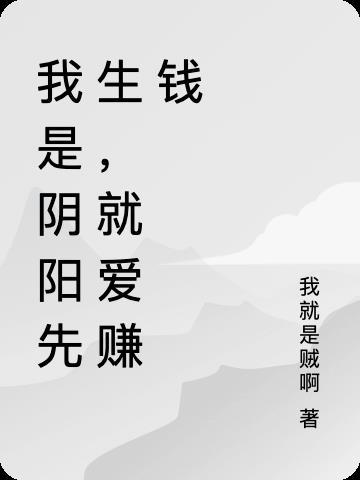69书吧>占有欲太强了叫什么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俗语说两个发旋的人脾气大,固执但非常聪明,李庭松一样样对上眼前的方至淮,他忍不住想,外国人也有这种说法吗?
但很快方至淮就站起来去拿回了医药箱,熟练地拆开药品给他冲洗消毒,李庭松并不排斥他的照顾,因为在安全方面,方至淮对他有着超乎寻常的在乎。
有一次李庭松在剧组遇见了威亚架子松动,当时方至淮正给他送饭,一看见架子塌下来,他立即拉开了他,有离边缘更近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压在了底下,李庭松立即联系了工作人员一起搬架子救人,但事后想起来又不得不心惊方至淮超乎寻常的注意力。
包扎完,方至淮没离开地方,只是回过头继续看着显示屏打游戏,背部似有若无的靠在李庭松的膝盖上,像是猛兽狩猎完成餍足的休憩。
李庭松又看见了两个发旋,他愣了一下神,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方至淮到现在也不过二十一岁的年纪,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不计后果勇往直前的。
只是他没有方至淮的能力和运气,而现在的方至淮不用忧虑钱财,也不担心前程,只一意孤行的随心而活,总是在每一个未知面前先一步迈出,然后再考虑前方是否是万丈悬崖。
第二天李庭松去见束弘方,束弘方的住宅在市郊,平时束弘方除了写稿子,大多时间都在打理自己的院子,李庭松去市场上挑了几盆花,到地方的时候刚好正午。
冬日的光照着人不热,凉凉地带着点干燥的浮尘在空中,漂浮成光斑。
他今早出门的时候方至淮也要出门,他还惦记着方至淮说他的那一句“不要管我”
,李庭松只顿了顿就出了门,也没问他去干嘛。
他捧着花盆敲了好一阵门也没见有人来开门,他把东西放在门口的架子上,给束弘方打电话,响过几声以后还是没有人接听。
也许到现在都没消气,李庭松垂眸看了看手机,正准备改天再来拜访的时候,身后的引擎声一响,束弘方开着车在他面前驶过,甩了他一脸尾气。
束弘方在他的车上下来,气哼哼的瞪了李庭松一眼,拿着花进院子了。
房门没关,李庭松跟着束弘方进屋,笑嘻嘻的问:“老师,最近腰好些了吗?”
“哼!”
束弘方推开屋门,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道:“我好得很!”
“我看见您院里还没翻土,我一会给你翻一遍再走。”
束弘方冷笑,“大冬天翻哪门子的土,你谈恋爱又谈傻了?”
“我哪有……”
李庭松脚步一顿,“……您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你谈恋爱的?”
束弘方砰的一声放下花盆,“你一谈恋爱就是这个蠢样子!你指望骗得过谁啊?”
“我不知道你这孩子是个什么毛病,挑的人个顶个的难办,你就不能找个老实人过日子吗?”
束弘方越说越气。
“姓齐的那个小子是个没心没肺的,现在这个好了,是个狼心狗肺的!天底下的男人死绝了,你怎么那么会选啊?!”
李庭松越听越心惊,束弘方的意思居然是不止知道他谈恋爱了,甚至连方至淮都认识。
他脸色逐渐僵硬,束弘方一个茶匙扔到他脑袋上,怒道:“你拉什么脸!你还给我看脸色,你知道我刚见了谁回来吗?”
李庭松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愣了愣,嘴唇蠕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方至淮,我刚刚去见了你搞的新麻烦!”
束弘方咬牙切齿,“你怎么谁都敢谈啊?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李庭松点点头,嘴上却麻木地问:“他是干什么的?”
束弘方冷笑一声,“他名下随便动用的钱都有上百亿,光靠钱也能挤兑死咱们了!”
他纳了闷了,“你到底为什么老是开这种食人铁桃花?”
李庭松虽然做好了方至淮家庭不简单的准备,但是没想到他是这种惊人的家世,他愣了两秒才问:“老师,他找你是想干什么?”
……
投资商,这年头钱多事少愿意尊重角色的投资商比天上的天上的月亮还少,束弘方的运转资金估算着根本不够,但是他又哽着脖子不愿意接受他看不上的演员。
接受投资就要改戏加人,束弘方本着宁缺毋滥,一直咬着牙不答应。
钱筹不来,虎视眈眈盯着他的人又给他施压,前几天他接到老朋友介绍,说来了一个外国人,只要票房分红,其他都不插手。
束弘方去了,会所包厢里,那个年轻人漂亮,强壮,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碧绿的眼睛像是华贵的宝石。
他心里松了一半,不是大腹便便的中年好色男人,年轻人的审美就算插手也不会太糟糕——只要没有难缠的情人。
直到男人张嘴,问他:“你就是李庭松的老师?”
束弘方好多年没有被人诘问了,他愣了一下,这才道:“他得罪人了?”
男人似笑非笑,“没有。我是他的爱人。”
束弘方脑子空白了一瞬,他在娱乐圈这么多年,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周围,服务生刚刚退走,要是关门的速度慢一点,就会清楚地听见这句话。
他皱起眉,不太高兴,“就算是,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男人摇头,“没关系,他又不红,我找你,就是为了说这件事。谈好了,你的新电影就有救了。”
束弘方严肃起来,“听小友的意思,我的电影还有没救的可能性?你的口气太大了。”
“是啊,你知道冯瑞吗?你感觉他这次的事情漂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