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书吧>贤妻电视剧免费观看完整版 > 第32节(第1页)
第32节(第1页)
想到被圣上养在外边的那个小杂种,太子的心如放在火上炙烤。
或许圣上早就有废了他的心思,宁栖迟才敢如此大放厥词,太子握紧手心,深知自己不能动手。
太子抬手挥了挥,暗卫一顿,接着将兵器收了起来。
“子念这话言重了。”
太子脸上重新挂起儒雅的笑,“人总会犯错,孤也未曾酿成大祸,怎么就使你我之间生了嫌隙呢?”
宁栖迟顺着台阶下:“殿下明白就好。”
一番客套,仿佛适才的弩拔剑张是空穴来风,直到说天色已晚,宁栖迟才要辞去。
他一走,满屋的陈设让太子砸的稀烂。
谋士踢开滚到脚边的花瓶,道:“殿下,小侯爷并未将这些事报给圣上,您言太过。”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太子威逼胁迫,已经触及了小侯爷的底线,即使宁栖迟趋于气势应了,也只会适得其反。
更何况,宁家小侯爷根本不惧。
太子将手掌的鲜血蹭在衣袖上,唇角的笑愈发森然。
他当然知道宁栖迟也许只是并不想站队而已,可他就是厌他高高在上的态度。
他不过是一个臣子。
谋士叹气,“如此,户部与宁家便算难了。”
定王还尚有办法补救,可若不能用太子的手凑成姜千珍和宁栖迟的婚事,那这两方怕是很难再有机会拉拢。
“孤如今确实对付不了他。”
太子想起那日韩府马车落水,他救上来的女子,“那庆元如何说的?他与姜千珍尚还有情?”
谋士一顿,庆元早被他们暗中买通,小侯爷与姜千珍在回门之日私会是他亲眼所见,且举止亲密胜似一对有情人。
太子虽然怀疑宁栖迟可能对那姜予达成了什么共识来坏他的事,但并不认为宁栖迟不想娶姜千珍了。
他只是不想借他的路。
太子神色阴冷,“那孤便让他哪条路都走不通。”
*
李氏去年在府里酿了几坛子好酒,这是姜予从二公子那听来的,说若是谁能挖到,便赏给谁喝。
姜予便惊奇道:“那这侯府岂不是要让人给挖空了?”
宁悸笑道:“母亲说若是下了铲子挖不到,就要罚一个月的月钱。”
那便是利益与风险并存了。
姜予不禁感叹道:“二伯母怕是要赚的盆满钵满。”
宁悸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母亲设了一道谜题。”
他想了想,复述道:“四坐鱼台对半两处,冬也不来夏也不来,举头正见人间月明,低首下闻百花盛开。”
这谜让姜予冥思苦想了一会,实在是辩不明白,便想投机取巧,“小叔可知谜底?”
宁悸手指抵唇笑了笑,“嫂嫂这可为难我了。”
正说笑着,二夫人便唤他们两进去,早起姜予有些庶务上的事要请教她,便在屋外跟宁悸说了会话。
一瞧见他们一道进来,二夫人嘴角就抽了抽,狠狠的刮了宁悸一眼。
宁悸朝她没心没肺的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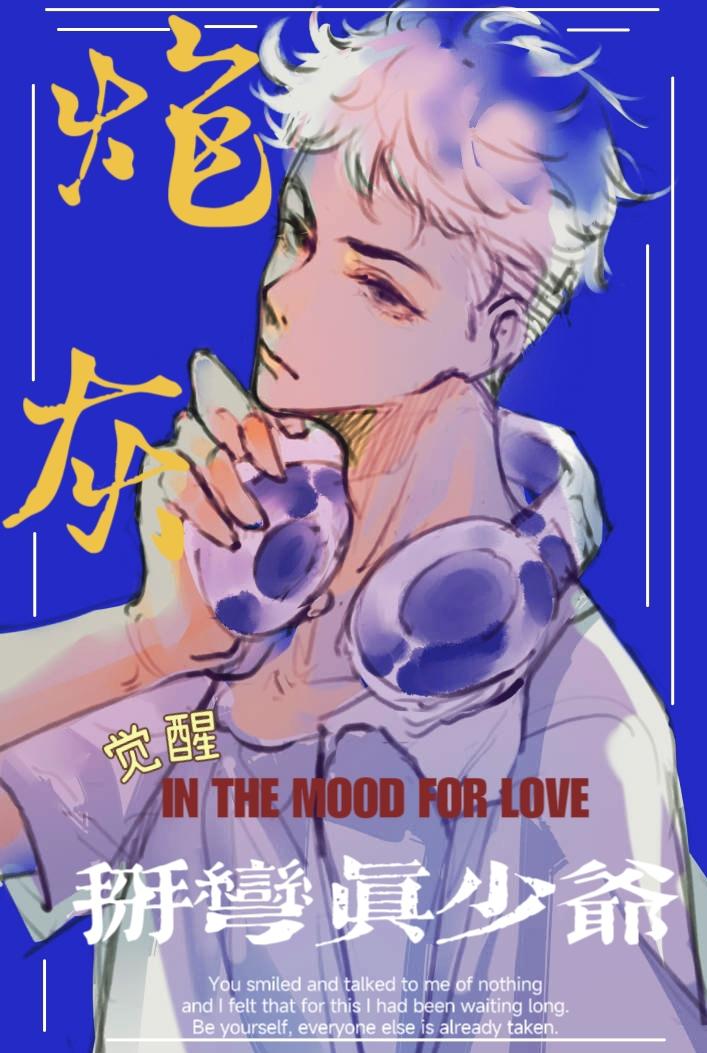
![[综英美]跟着红桶学做人](/img/1784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