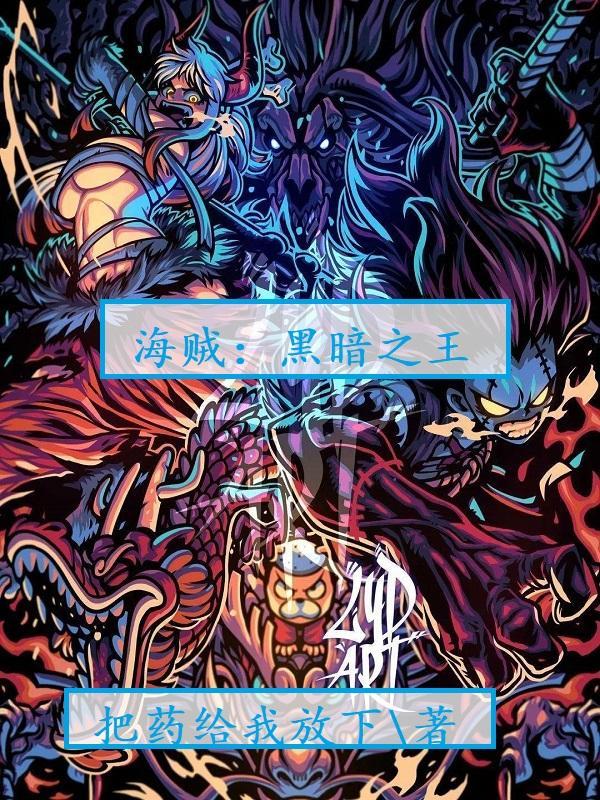69书吧>遗山诗集 > 第60章 算得失三(第1页)
第60章 算得失三(第1页)
作为中山的掌权人,原遗山这三个字,是时时被迫与集团绑定的。
他的一举一动,意味着股价的涨跌,市值的变化,而这背后身系的,又是集团上下数不清多少张等着吃饭的嘴,以及每一个行业内举足轻重的项目。
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也是为什么,原遗山始终小心翼翼,未敢将自己的病况透露给外界的原因。
中山的掌权人不能是个疯子。
同样,中山的掌权人,也只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组建一个足以令上下信服的、安定的家庭。
原晋中根本不用摊开了说,可意思已经放在那儿了。
——你最近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有哪些头脑发热的举动,我都清楚。
——我之所以没去干涉,是因为相信你有大局观。
多可笑,他被架上龛台,要求到死都做一尊佛。
离爱,离恨。
一个,彻头彻尾的工具人。
离开书房时,他发现博山炉的烟又熄了。
他只略微缓了下脚步,随即推门而出。
下楼的时候,原雪礼和邵昊英已经不在。
司机取了车,他坐进去时,窗边覆下一道阴影,偏过头,透过茶色的车窗,看到邵昊英屈指敲了敲玻璃。
原遗山降下半截车窗,顿了顿,又吩咐司机下车。
“我自己开回去。”
等司机走了,原遗山才开口问:“有事?”
“回个家也用司机,不像你。”
邵昊英抬眉,“听说你这两年连跑车都不开了。”
原遗山沉默,眼神明显不耐,是“有屁快放,我赶时间”
的意思。
邵昊英佯作无辜地摊了摊手:“只是有个问题想问。”
他说完,见原遗山不为所动,便装模作样清了清嗓子:“你和那个Iris没什么吧?要不是你马子的话,我下手你不介意吧?”
原遗山目光渐冷,语气是克制之后的森然。
“你够胆的话,可以试试看。”
“发这么大火干嘛?”
邵昊英失笑道,“原遗山,先不仁不义把我扫地出门的,不是你吗?”
车门猛地推开,躬身说话的邵昊英躲闪不及,被撞了个正着,趔趄了两步,半天没缓过来。
接下来一脚直接把他踹倒在地。
疼痛使他本能地身体蜷缩,咬着牙正要撑起身,领口就被猛地拽住,直往上拎,他喉咙一紧,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耳边的语声却慢条斯理,十足冷静。
“这么一说,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邵昊英。”
“当年月光给你的马策骑,和她后来跳港,到底有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邵昊英顶着一头冷汗,眯眼看着上方的原遗山。
男人甚至连衣襟都没皱,与他狼狈躺倒疼得冷汗直流对比鲜明。
可邵昊英居然不觉得生气,甚至还有点不知打哪儿来的兴奋。
“她没和你说过。哈哈……”
“她连这个都没和你说过?”
“那丫头,不是那你一手养大的吗?我还以为……你们关系不错呢。”
邵昊英扯着唇,脸上满是笑意,一边疼得抽着气,一边挑衅。
“原来你们也不过如此。”
“亏她那时候……还把你当个什么东西供奉着,真是让人不爽——”
领口又是一紧,邵昊英剧烈地咳了几声,忍不住握住对方铁一般的手腕,试图挣扎,竟在对方盛怒中的力气前败下阵来。
“少爷!这是怎么啦?使不得呀!”
这里的动静不小,惊动了佣人,找来管家赵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