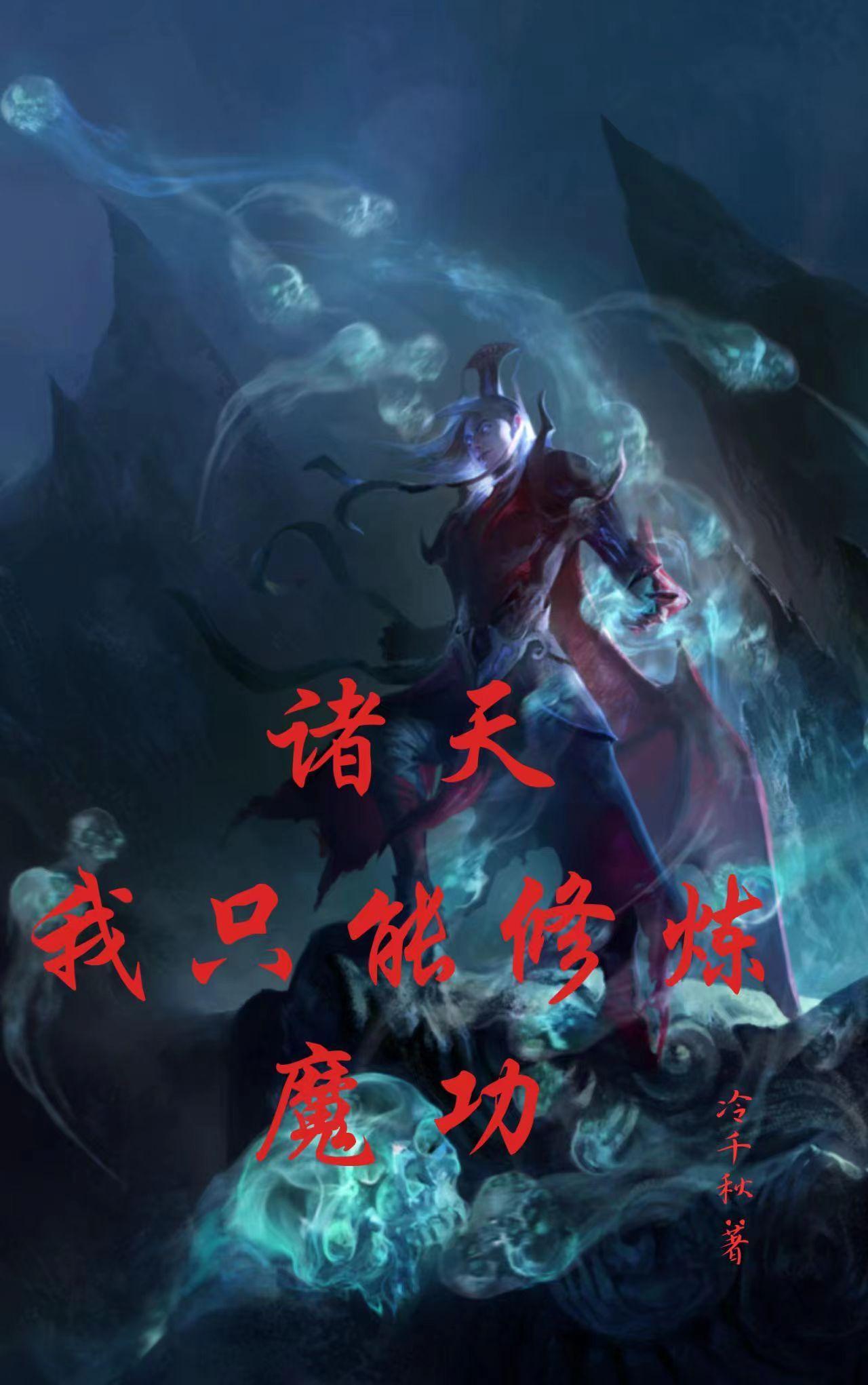69书吧>风流皇女她只想躺平(女尊) 葡兮 > 第40章(第1页)
第40章(第1页)
她睁开因为过度充血而有些昏花的双眼,朝门口投去目光。呼的一声,门口之人吹灭了蜡烛,整个屋子霎时间黑暗了下来。“追月?”
应如风有些怀疑地问道。在刚刚那一瞬间的光亮里,她似乎看到了追月的那身白衣。来人没有应声,疾步朝床前走来,俯身拥住了坐在床边的她。清新的竹香如烟海般笼罩住她,丝丝缕缕浸入口鼻之中。应如风脑海中划过一道白芒,轰地炸开了。这是怀星惯用的香,是她亲手所赠,决计不会认错。解情蛊应如风迫不及待地揽住身前的人,翻身压在了身下,覆在他的耳边贪婪地汲取着他身上的气息。清冽的竹香与澎湃的情潮碰撞在一起,一冷一热交替反复,难耐的燥热似乎有所缓解。应如风紧紧地抱住追月,脸贴进凹陷的肩窝中,嘴唇抿上那片凉凉滑滑,让她很舒服的冰肌。身下之人异常紧张,身体抖个不停,颈上的每一次吮吸都会让他发出醉人的幽咽。鬓边卷翘的碎发若有若无搔在她的颊上,痒得她浑身发颤,应如风曈眸中的猩红又深了几分。她捏住吹弹可破的脖颈,拇指拨弄着滚动的喉结,暧昧地唤道:“星儿。”
床单被抓得皱成一团,追月颤动着仰起脖子,齿尖深深地咬入下唇中。他好想开口求她,不要在这个时候喊别人的名字。他会崩溃。应如风伸手插入柔顺的发间,扣住他的后脑,低头吻住了温热的嘴唇,舌尖轻轻一挑,便将带着齿痕的下唇解救了出来,含在唇间轻轻舔舐着,令那凹陷处缓缓弹起。交缠的涎水声裹挟着不轻不重的喘声在房间里蔓延。“怎么紧张成这样?不知道还以为是你中药了。”
应如风笑着抓住追月的手掌,把发皱的被单从他的指缝中拯救出来,取而代之地与他十指相扣。明明屋中漆黑如墨,只能隐约看到彼此模糊的轮廓,追月却扭头将半张脸埋入床间,害怕脸上的滚烫被她发现,更害怕她发现自己不是她想要的人。追月紧紧抓着应如风的手,贪恋着未曾体验过的温度。温润的指尖在她的手背上轻轻磨蹭着,那是他从未触及过的地方。他仿佛一个小偷,只有在黑暗中才敢把偷来的宝物放在手中摩挲。
应如风狡黠地弯起眼睛,含住呈到她面前的耳珠,毫不怜惜地衔弄住,放在舌尖挑逗着。略微有些尖锐的呜咽声隔着被单传出,追月如同一只被人制住要害的小兔子一般,在她怀中缩成一团。应如风咬出一道浅浅的齿痕,感到身下之人绷得如同拉满的弓弦,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他,抬手轻抚着他的发丝,低声唤道:“星儿。”
她不无怀念地说道:“想当年母皇命我去丞相府拜见你母亲,我本觉得无聊,一抬头却看到你在阁楼上偷看我。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追月没有做声,呼吸声中染上了一丝哽咽,应如风也没有在意,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我在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灵动的眼睛?”
应如风满眼缱绻,手指在他的眉眼间勾勒着,连声音都变得温柔了许多,“母皇命我常与你哥哥相见,我可不愿跟个只会说教的闷葫芦约会。本想着找借口敷衍过去,不曾想他总带着你一起出来,我就忍不住答应了。”
追月嘴中发苦,他如何不知她想见的是谁,害怕她拒绝自己的邀约才总是带着怀星。每一次他都会变成多余之人,看着两人在自己面前谈笑风生,他却连一句话都难以插进去。应如风那时总夸他端方严正,不愧是京城贵公子的楷模。他表面没有波澜,心中却忍不住暗喜,毕竟老成持重历来都是当家主父的必备品质。他不曾想过这些话全是客套话,应如风喜欢的是跳脱的性子。一道湿痕从应如风的指腹流过,应如风掰正追月的脸,吻掉挂在眼角的泪珠,“都怪我当年一时情难自已。我本以为凭我的身份,就算不能恢复你曾经的荣华,也总能护你一辈子无忧的。可惜世事无常,以后就把我忘了吧。”
应如风莫名地有些害怕听到对方的责难,吻住了他霎那间变得冰凉的嘴唇,伸手探进了他的衣襟。情蛊发作的越来越厉害,应如风不再压抑自己,手上的动作渐渐粗暴起来。一件件衣物从床帐中飞出,叠落在地面上。凌乱的床单随着床榻的摇摆慢慢地向地上滑去。不知道是否因着情蛊的缘由,应如风觉着怀星今夜格外的美味,她似乎没有餍足的时刻,一遍遍将他拆骨入腹。五指嵌入薄如蝉翼的肌肤中,他的声音起初还是细碎的呜咽,继而变得粗重,如同雨打芭蕉般越来越快。只是不知为何,无论她怎样摧残,他都一言不发,绝不求饶。他越是隐忍,应如风的兴致越是高昂,一遍遍拉回想要逃跑的猎物,不断地加重惩罚,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留下一道道青红印子。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她体内翻涌的气息才平静了下来。眼皮沉重地像在打架,应如风胡乱地拉过被子,盖在两人身上,拥着对方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