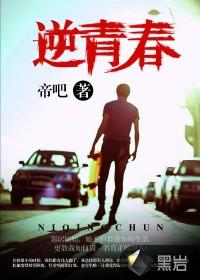69书吧>梅花落南山情侣网名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人是活的,房子是死的,人都走了,还看房子做什么?
但她无意为自己辩解,淡淡地说道:“让你失望了,我确实是薄情的人,不喜欢睹物思人。”
他的笑容里泛着苦涩,低头不敢望向她的眼睛,说道:“你为什么连演一下都不愿意呢?我连被你骗一下,敷衍一下的资格都没有吗?只要你说你曾经回来过,那我一定会边骂自己傻子,边无条件相信你。”
“自欺,有意思吗?”
她的声音波澜不惊,像是事不关己。
“从来和你有关的事,我一向乐于自欺。我靠着自欺,度过了失去你消息的整整七年。”
她的眼底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竟问道:“怎么骗自己的?说出来听听,让我看看你编了什么样的故事给我?”
他不答她,径自走到餐桌前,桌上铺满了整桌的牛皮信封。有的邮票已经起胶,有的邮戳已经模糊不清。
她拿起一封信,地址写的是这里,收信人是她。邮戳的时间竟然从2012年一直持续到了2018年,也就是说整整五年他都在往这里寄信,应该是负责打扫这里的人代收了信。
她不知道他怀着什么样的信念这样坚持了六年,
她想拆开手里的这封信,想读读他都写了什么给自己。她想看看这一桌子信里,到底是咒骂多,还是思慕多,到底是恨多,还是爱多。
他却稳稳地捏住了她手中的那封信:“礼物当面拆是一种礼貌,但是信这样私密的东西,当面拆可就是不顾写信人的体面了。”
她问道:“既然不想让我看,为什么还要写?”
他自嘲地笑道:“我觉得我写这些信的心态就像狱里给波西写信的王尔德,在信里恨得有多骄傲,背地里爱得就有多卑微。”
“王尔德?谁?名字取得不错,我还以为姓王的名字都像我爸一样土气。他爱人的名字好奇怪,是少数民族吗?”
“……王尔德不姓王,他是个爱尔兰作家。”
“哦,原来是个英国人。”
潘纯钧欲言又止:“……也不能说你错,因为那时候爱尔兰确实是在英国治下。但是答应我,将来你出国了,千万别问爱尔兰人你是不是英国人。”
“哦,好。那他干什么了,怎么进去了?”
“因为爱上了法律不允许的人,因为十九世纪的同性恋在英国还是一种有伤风化的罪行。”
“扯远了,说回我们。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写了六年信,还是在明知我没有再踏足这房子的前提下?明知不会收到回信,但还是要写?”
“什么力量?你真是明知故问的高手。当然是爱,是不知所起但一往而深的爱。我多么擅长自欺,明知你不会回来,但还是一封封往这里寄信,让打扫的阿姨帮忙把信堆放在显眼的地方。我骗自己,万一有一天你打开了那扇门,万一你回到了这间我们同度过四年的屋檐下,你也许会读到那些信,你也许会联系我……”
她又问道:“那2018年以后呢?怎么突然停止了?是不知所起的爱突然不知所踪了吗?”
“我已经用了六年来证明爱,为什么不能用一年来证明自尊呢?你这样问我,未免太残忍。”
她戏谑他道:“可惜了,先爱的人,哪里还有什么自尊?如果你真的怜惜你那颗自尊心,你根本不会回来,不是吗?”
他静静地凝望着她,他的目光想穿透她,看透她,却一次次被强硬坚定的她弹回来。本来抱着自伤一千也要损敌八百的心去爱,奈何对方到头来毫发无损,他却丢盔卸甲。
他望着她有恃无恐的模样,物理高度上是他在低头看她,可情感高峰上却是她在俯视她。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大抵是这么个意思。
他的手抚上她散落的发,青丝从掌心穿过又滑落,一如明知流沙会逝于掌心,虽留不住,但还是贪恋手心有过的温热。
他的声音不徐不疾,带着几分自弃的说道:“没错,和被爱比起来,自尊算什么东西?我就像家里那扇门,只要你愿意尝试,你就会发现它的锁芯从来没有变过,永远为你等在原地。”
她任由她的发丝一遍遍被他的手指穿越和抚摸,她也不打断他,而是低头按时间排列组合着桌上的信。
她突然昂头,声音里有着不容置疑的笃定:“既然是写给我的信,那我就有权利阅读。所以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带走这些信。”
他拨弄着她头顶的发丝,温声道:“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即便你的骄傲要从我的骄傲上碾过去,我也不会说个不字。”
谢巾豪忽然有种冲动,她想接受他明目张胆的爱,凭什么她就不能抛开那些顾忌及时行乐一回呢?这样他进一步她退一步的,又有什么意思?人生短短几十年,她还有多少时间能好好享受爱和被爱呢?
故人归(二十一)
谢巾豪还是低估了颜值在这个时代可以吃到的“红利”
,或者说会因此背负上的压力。
她上一次在镜头前对答如流的从容自信为她圈到了不少路人的好感,以至于局里有意安排她开通抖音和b站的科普账号,平日里进行一些线上的面向群众的普法教育。
谢巾豪一开始是拒绝的,这任务找个有亲和力的女警明显更合适,干嘛非得是她呢?但是她妥协了,毕竟她一直是被照顾的那个人,做点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也是分内之事。
不过她和领导因为账号的取名产生了一点不愉快。局长的意思是直接叫“警花说”
,言简意赅,账号的功能属性也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