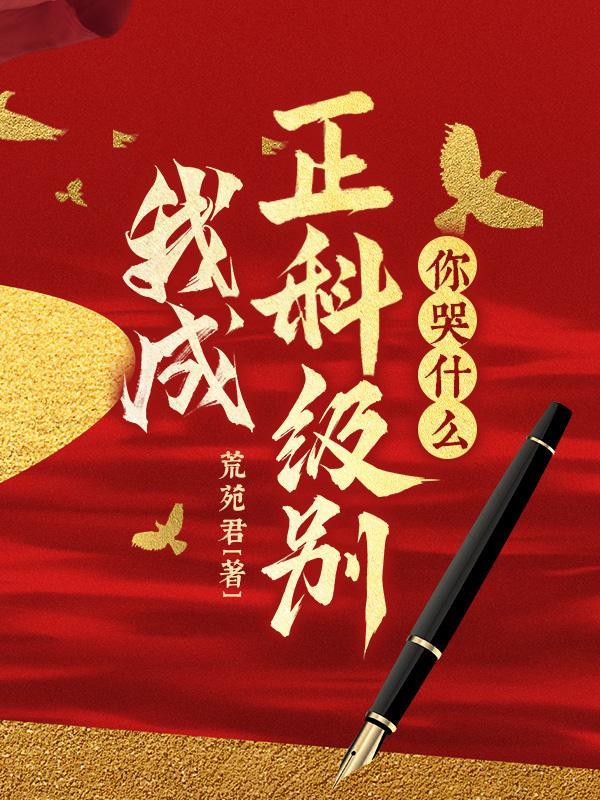69书吧>瀚海义符by张勉一讲的什么 > 第53页(第1页)
第53页(第1页)
那青骢马疾奔几步,面前正有个白狄兵正在抢一个少女,另外几个则持着弓箭指着另外两名牧民,大声骂道:“你们不听不里耳的命令,胆敢私自迁移,明明家中尚有好几名男子却也不来兵营中报道,还不知罪?”
但见那两名牧民一老一少,老的头花白,小的也只十二三岁的年纪,被两名白狄兵欺辱得又怒又怕,那白狄老者则闻言急得大叫道:“我们随你们去当兵!我的女儿,你可不能抢走!”
那白狄兵却喝道:“你们违背了断事官的命令,全家都要处罚,这个小姑娘也要带走。”
阿术真大怒,立时又拍马上前,一马鞭便抽向那白狄兵,直将他打得脑浆迸裂,那白狄少女却趁机跑了开去,回到父亲身边。
这群白狄兵大惊失色,转头去看阿术真,又见他那坐骑青骢马毛光亮,甚是雄健,显然是匹难得良驹。白狄人嗜马如命,几名白狄兵原本还有些惊惧,这时却又贪念大动,怕伤了马匹连箭也不,径直持着刀兵一拥而上,纷纷大喝道:“哪里来的混小子!给我拿下了!将他的马也拉去充入军中!”
阿术真信手拍出数掌,看似轻飘如云,实则掌力却是阴寒无比,所用的正是波旬寒冥掌的毒门重手法,眼见他手下绵掌使得行云流水一般,顷刻间就将那群白狄兵打得头骨碎裂,倒毙地上。
众牧民见那群凶神恶煞的白狄兵瞬间身如软泥,倒毙而死,然则却连一丝鲜血都无,一时间又是骇然又是错愕,一个个都呆若木鸡,过了好久,这才恍惚回神,忙又上前向阿术真道谢,口中连称:“圣火不灭,阿密特庇佑他的子民,不教恶人欺辱。”
“圣火不灭,”
阿术真翻身下马,也以金乌教的教礼姿势回礼,又问那白狄老者道,“额格,这群恶鬼何故与你们为难?他们说的断事官之令,又是怎样一回事?”
伊特赛语中额格原是用来称呼叔伯之言,但在桑珠乌仁旗这一带,但凡见到长者都可以称呼为额格,正是桑珠乌仁旗一带人说话才独有的习惯。
那老者原本见阿术真穿着汉人装束,一手武功又十分可怖,心下正自惊疑不定,虽是他出手相救,却仍自对阿术真颇为戒备惊惧,唯恐是“方出虎口、又入狼窝”
,但眼下听得他说伊特赛语十分纯正,似乎也是桑珠乌仁旗一带的人,且见礼颇为客气,似乎不像要再行恶行的模样,这才稍感心安。
那老者答道:“断事官跟着大汗西征回城之后,便立时下了一道命令,说是今冬一律不准南迁,等大汗点兵之后,才准到南边牧马。唉,他们抽兵也真狠,我们桑珠乌仁旗的年轻后生几乎全都给他们拉去当兵了。我先前两个儿子早已西征死在沙场上了,眼下就只这一个小儿子和这个小女儿,若然小儿子也被抽去当兵,那我和女儿如何还有命活?这才逼不得已,悄悄逃了出来,若被查到,就只说南迁得急了,还不知道断事官的指令。谁知他们根本不容分辩,抢了我们好几头羊就算了,还要来奸污我女儿。”
阿术真听了,却不由得心下一凛,心道:“乌尔忽近来西征才吞并了西戎诸部,可说是大获全胜、凯旋而归,他为什么又如此着急要来征兵?他又在谋划什么战事么?”
他想到此处,心中顿觉不妙,深深蹙起眉头,决意要探明此事。
他与众牧民又闲话几句,探听了一阵高罕锡林城的情形以及不里耳近况,心下了然,便与众牧民道别,跟着从那群白狄兵的尸身上取下衣衫,匆匆改装,又轻骑上阵,驱马奔至高罕锡林城。
那高罕锡林城中百姓来来往往,把守却并不甚严密,而阿术真假扮作了兵丁,混进去也就十分轻而易举。
他入城之后,先探明了不里耳所在,用假身份在一家客店投了宿,白日里便去隔壁的铁铺,要铁匠给他打了不少暗器。店中铁匠见他一身兵丁装束,只当是军中所需,再者阿术真出手阔绰,一片金叶子使下去,他们自然是无不遵从。
到得次日初更时分,阿术真携了玉昆刀与暗器,径直来到不里耳所住的宅邸外。
不里耳心思缜密,府外的守卫也是颇多。阿术真拉上黑色面幕,掩住口鼻,悄无声息地蹲在不远处的檐顶,待得那一班的卫士巡过,施展轻功纵身一跃,栖身便跃入了府邸之中,跟着手中挥出一把银针,将在墙内的守卫也悉数射倒。
阿术真闪身掠地疾走,绕过数处房屋,又见两名侍女手里拿着烛火,正自引着三名官员、两名武士过去。
他眼见人多,倒是不便出手挟人过来逼询,径直蹑足在后跟随,只见那几人走向一座大殿,进得殿中去了,殿外匾额上悉数也都是弯弯曲曲的伊特赛文。
阿术真心道:“如今月上中天,不里耳还叫一群心腹来他宅邸之中密谋,此事必然事关重大。哼,不知这奸贼又在打什么歹毒心思。”
他屏息凝神,又从袖口中摸出一把银针,跨步上前,将手中银针一一抛出,悄无声息地又放倒一批守卫,跟着抢到墙边,足尖轻点,使出“跳润飞崖”
的轻身功夫,瞬间沿墙而上,到了殿顶,伏在屋脊侧面,在四下环顾一圈,见得四周再无守卫可察,便轻轻拉开殿顶的几块瓦片,从缝隙中凝目往下而观,跟着附耳贴近缝隙,凝神听去。
只见满殿烛火明晃晃的,居中坐在胡床上的一名精瘦汉子正是不里耳,其余心腹大臣与武士则均围坐在侧,众人正自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