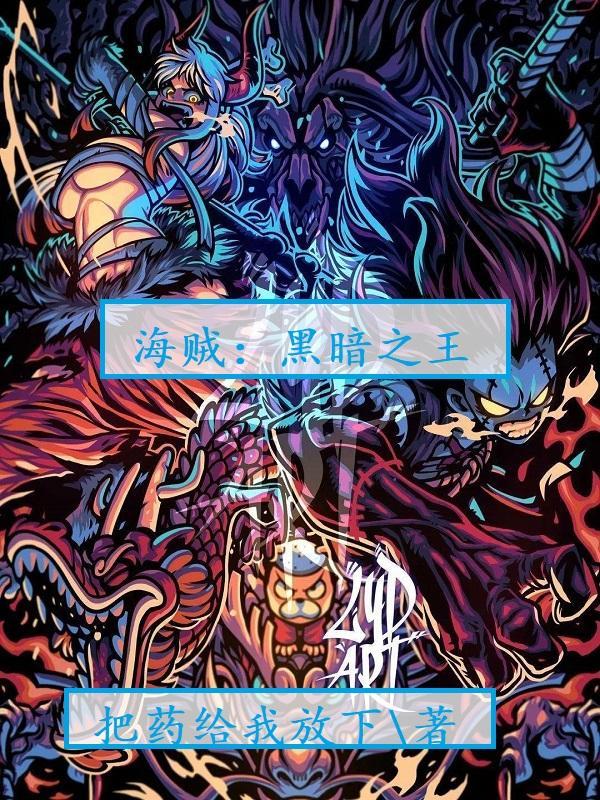69书吧>公主男为请赐公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文延乐做了一个深呼吸,而后慵懒的吁出了那口长气:“不要,若我为帝,也只得你一人。若我为你夫,只怕你就要三夫四侍了。”
他垂下眼帘,低沉温柔的问:“咱们一心一意,相伴白头,不好吗?”
真是缠绵悱恻。有那么一瞬,是很吸引人的。
三年来的耳鬓厮磨,夫妻情分并非没有分量,但画面很快变成了死去的胡八,死去的胡七与女乞,死去的‘公主’,三次重击之下,那些美好画面顿时支离破碎。
张凤起的目光黯淡下来,心中做出了无声的回答。
被文延乐困住后,张凤起并没质问其用意,每日在船上嗑着瓜子,喝着热茶,眺望河岸风光。她不问,文延乐自然是不提,两人若绕开这些事儿,倒也相处得浓情蜜意,有如新婚出游的夫妇。如果忽视满船所载的羽林卫的话。
只是这几日张凤起这边是云淡风轻,都昌与长安却又是相反模样。
文延乐虽然没动那艘浩大的官船,却将船上软禁的几位知府、县官都放了回去,等这羽林卫一走,丁毅等人再去擒,早就晚了。
倒不是抓不到这些人,而是没必要再抓。有关公主遇刺身亡的消息,早就传得惟妙惟肖,成了都昌城里最人所周知的秘密。
为免谣言传至京中动摇人心,卢兴元等人自然早派了人往京中送讯,只是这讯息还没送出都昌,就被人所斩劫。
于是谣言比真相先一步到达了长安,几乎成了铮铮事实:姚相派了一品堂的人刺杀公主身亡。
霎时,京中本不平静的局势更为波涛汹涌。
“这可如何是好?公主……”
夏晋卿急得一身冷汗,握着折子的手些微发抖,除了他,室内一众公主的门下之臣,面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莫不如丧考妣。
宋莞站起身来,沉声道:“事到如今,咱们群龙无首也不是办法,总不能任由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如今京中局势一触即发,夏皇后与姚相在斗,胜负未定。也只有文家置身事外了,咱们此时没了公主,实在是势单力薄,不如咱们另投……”
此话还没说完,原本泯于众人的马义忽然出现在宋莞身侧,一道长剑立马横在他脖颈处,寒光闪闪。
“你!你这是做什么?”
宋莞怒目圆瞪,道:“别以为你是公主跟前的……”
“是啊,别以为你是公主枕边人,便可耀武扬威!”
“现在公主都不在了,你这是以下犯上!”
宋莞身侧几个近臣也站出来仗义执言。
马义面不改色,自接管刑部以来,早非当初懵懂怕事的小家公子。他与对面不动声色的贺莲相视一眼,抬手一沉,剑锋便埋入宋莞的脖子。他只来得及“啊”
一声,便在血泊中瘫倒在地。
四周臣子大骇,在座文臣居大部分,哪里亲眼见过这样血腥场面,莫不白了面色,四肢发抖。
贺莲这才站出来,看也不看地上的尸首一眼,不紧不慢的道:“众位大人,公主不过诈死一回,就有人按耐不住了,妖言惑众了。”
薛川是头一个稳住的,他跟着道:“这宋莞平日就与文家多有勾搭,果不其然,公主一试,就试出了他的马脚。”
他狭长的眼一眯起,低声道:“就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与他是一丘之貉了。”
方才那几个与宋莞帮腔的人立马坐不住了,面面相觑下,慌忙着道:“公主……公主如果不是真的被刺身亡,怎么不见卢兴元的音讯?”
“可不是,听说公主的尸身都已经由陆路北上运来了。”
“圣上也正让拱卫司的人彻查此事呢,徐达都被派去两江……”
你言我语之下,原本稳定的情况又发生变化,其他观望的几个臣子似乎都有了迟疑。
贺莲仍是不慌不忙,从袖口里掏出一封书信来,缓缓展开道:“这是公主的亲笔书,就算字迹能作假,辅国公主玉印是不能吧?”
众人一一看了书信后,终于是没有异议。
贺莲稳定了场面,也不托大,仍将话事权交给此时众臣之首薛川,恭谨道:“如今场面下,还请薛相爷理出个法子示下。”
薛川到底老姜尤辣,不动如山,只问:“贺御史,公主的吩咐是?”
这话一出,俨然是明白眼前的贺莲才与公主心意相通,不过书信之事后,众臣也认可了贺莲的位置。
贺莲谦辞了一番,才道:“公主早有安排,目前已经收到太医院的风声,且不说二殿下时日无多,就是眼下被指买凶谋害公主,姚相清流一党,已不足为患。”
众人也颇以为然的点点头,薛川则道:“少了一个清流党,还有夏皇后,据我所知,夏皇后与文家早就私通款曲,想必大家也看出来这段时间姚相之所以落了下风,文家的暗中协助,可是功不可没。”
“的确,连咱们这里都混入了文家的人,只怕他们的野心也小不了。”
夏晋卿此时也冷静下来,众人也开始分析眼下的局势。
贺莲看了一眼地上的尸首,适时道:“如此,咱们不妨祸水东引,用它来为夏皇后与文家制造点事端。”
众臣若有所思,这时却听得外头一声禀告:“众位大人,奉国将军来了。”
张凤起与文延乐行了几日的水路,她原以为对方会转上岸,毕竟水路实在很有些慢。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急,张凤起悠然,他比张凤起更悠然。
这日,张凤起闲来无事,在一只瓷缸里逗弄几只大鲤鱼,一片馒头都引发几只肥鱼争夺得十分来劲,拱来拱去。
文延乐过去抱着她,头埋在她脖颈处,深深吸了一口,才道:“你不问我有何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