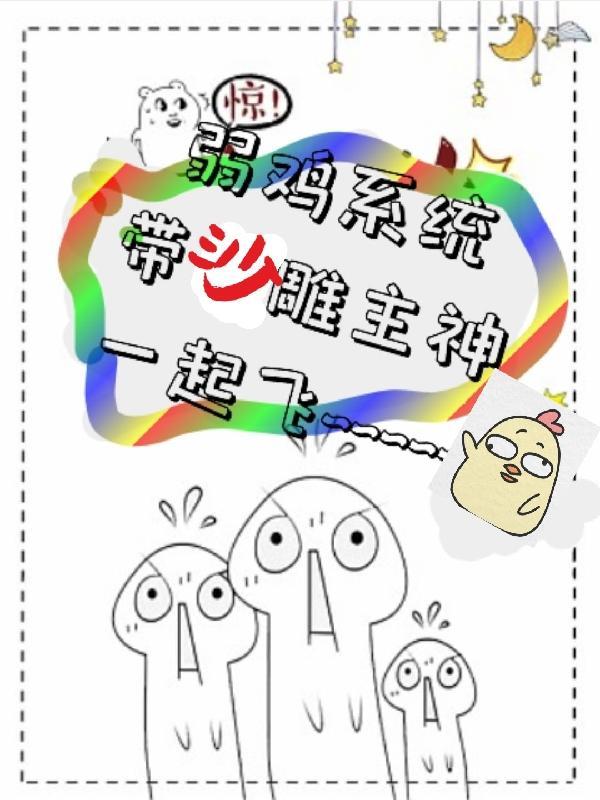69书吧>在水何方什么意思 > 第13章(第2页)
第13章(第2页)
这时朱氏又走出来,手里拎两只荷包,上头俱带银线暗纹写就的“酉”
字,布丝虽老旧,却完好无缺,一看就是多年前的旧物。她当魏酉和魏储依的面分别掂了掂,一只微微趁手,另一只轻飘飘的,她就站在门口,皮笑肉不笑地看魏储依,语气毫不掩饰讥讽,“用的差不多了反倒说分文未动,别以为我不知他到底给你多少,说难听些,买下这处废宅也尽够了,你大伯说你是读书人,原来圣贤书竟是把你教成谎话连篇,不孝不义的小人!”
魏酉高声喝断,“莫要胡言!还不屋里去!”
所谓给魏储依兄妹的接济,旁人不清楚原委自己自然门清,第一回,他对自己那英年早逝的弟弟也有痛心,所以给的多些。第二回,他买卖赔本,需要现银周转,是以给的便少了。这些朱氏原不知情,眼下更无从言说,见两只荷包原原本本放在那,一时间大感羞愧难当。
魏储依脸色淡淡,只看魏酉一眼,背十七往院门外走。
魏酉尴尬招呼,“屋子该是快打扫好了,这会往哪去?”
魏储依背身冷声道:“劳烦大伯看我父亲面上,给我兄妹二人一条活路。”
魏酉讪讪,“这是甚么话,一笔写不出两个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
魏储依回头看向卧房,魏酉忙道:“等水彻底退了大伯就搬出去,只你祖母毕竟是长辈,又身子骨不好,定是要睡卧房的,你看…不如叫十七和你几个妹妹都跟着你祖母…”
十七在魏储依耳边轻轻道:“我只和兄一起。”
要十七和钱氏一屋相处…魏储依眼前闪过昔日钱氏辱骂十七的情景,顿觉荒诞不已,他托起十七小手紧攥成拳,沉默好一阵,终是长长一叹,“罢了,我带十七睡灶房。”
魏酉夸赞的话还未出口,便听少年正色说道:“大伯莫忘了自己刚刚话,水一退,便都搬出去。”
魏酉连连点头,“自然,自然。”
和州这场水患是建朝以来最大的一次,深究细看,不只是天降灾难,实则也是人祸横行。
重灾区百息令朱迟泳未对灾情做出任何举措,反而敛财逃遁,致使百息县数千人流离失所,幸而和州州府大举赈灾,虽惨祸已酿,然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这场灾害尚未造成流民叛乱之祸。
天下事纷纷攘攘,和州水灾不过九牛一毛,至多成为和州州府上表天子时酌情添加的一笔,加之有人有意压下,在朝野上下未出任何水花,而百息县很快就有新官上任。
魏酉也得到朝廷给灾区商贾分的补资,他元气大伤,这么点银钱根本无济于事,想要回到富甲一方的鼎盛时期,却再无可能,甚至连重新开始经商也难实现,区区二两银补助,一家子嚼用都不够,还能做甚么?
魏酉在上阳城府衙足足占两个时辰,最后不得不认命,加之钱氏拿出的十两,他在桃溪镇买下一座小院,再置一些家什,银钱尽花光了。
新家窄陋,原是一家店铺倒闭而改成的屋舍,只有一间卧房一间灶厨,整体院落比魏储依的还狭小。
镇头的那院舍确实属于魏储依,曹贞贞病时亲自带他办的文书,从户主魏旬过到长子名下,依照晋律法:“兄弟成年而分。”
魏酉一家长期住那触犯律法,于是买妥新家,魏酉便主张搬过去,只是新家住不下那些人,魏酉夫妇同钱氏商量,他二人带几子搬进新家,钱氏和魏酉几女继续住魏储依那。
魏储依得知一阵无言。魏酉一家挤在这座院子的数月,他无数次想起魏旬夫妇离开的情景,他听见钱氏打骂魏酉几女,第一反应便是紧紧捂住十七耳朵,这些天从未让钱氏见过十七,就连他自己碰见钱氏,“祖母”
二字也无论如何唤不出口。这些人都是他名义上的亲人,却更像他的仇人,否则哪有亲人会坑害自己家人。
可笑又可悲的是,钱氏至今不知魏旬夫妇都已离世,甚至在她不时的咒骂中,还能听到魏旬夫妇的名字。魏储依觉得自己性情太过冷持,明明这时他该怒火丛生,而他却只是面无表情地远远避开。
县试如期而至,只需一日,就在家附近。十七一定要留在官学外,从早到晚守在门口,饿肚子时,还是李清源给她拿来两块糕饼充饥。
十七只吃一块,另一块留给魏储依。
不出几日,官学张贴红榜,魏储依和李清芳都在榜上,九月再到和州府参加院试。
夜里十七睡下,魏储依在一旁呆坐,朦胧夜色中,那张秀面有甚么情绪起伏不定,直至天色微明,他终于下定决心,望着正睡香甜的小小姑娘,自言自语说:“这世上,魏储依就只有十七一个亲人了。”
他细看那张睡梦里的稚脸,“所以一定要十七过上好日子。”
天大亮,魏储依少见地叫来魏酉,两人关在灶房里说半日话,魏酉出门面上挂笑,走出老远还在连连保证,“小依放心便是,大伯定不负所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