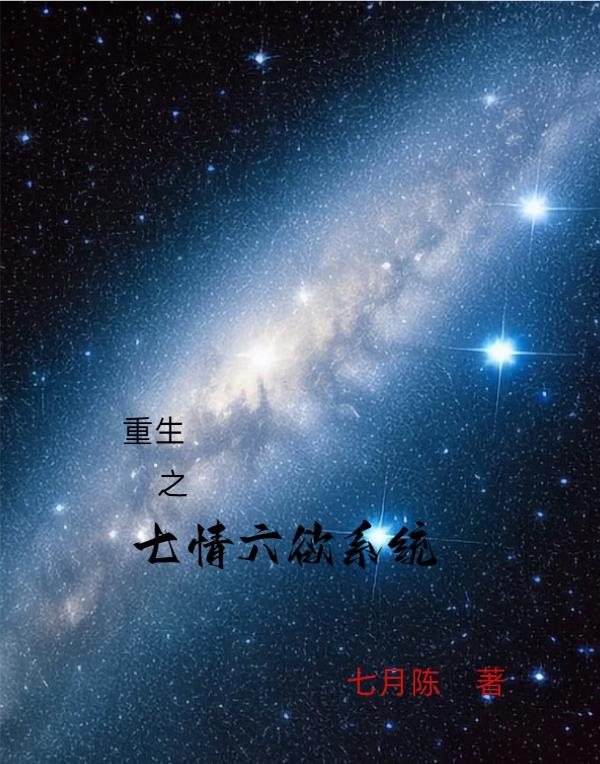69书吧>和肖邦弹风谱月的日子 sherlor > 第20章 EtudeOp 20(第1页)
第20章 EtudeOp 20(第1页)
【想见你】
肖邦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因为一个人,迎来嫉妒自己、讨厌自己的一天。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并不是个好相处的人。
像他这样敏感又缺乏安全感的人,完全就是只刺猬。因为会刺伤别人,因为害怕人群,他从不过多地靠近。不论是沙龙还是社交,他向来都把距离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维持着他自己最习惯的节奏。
好奇心不属于肖邦。
和他的音乐口味一样,他偏好古典的、规范的,对新潮的、实验的东西兴致缺缺。注定了流浪的诗人,也从不考虑要把心的归宿放在哪——他好像爱过人,又好像没有爱过。除了他留在纸上的文字,还有音符里的那些乐句,他从未过多表现过爱情的冲动。
理性属于肖邦。
他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在夜色里归于平静。连同那些所谓的心动,除了在他的篇章里留存,几乎不会被他沉溺回味——他也许偶尔会提及,但或许更像是在调动一个作曲家的本能,回忆如何用音符去表达悸动。
欧罗拉是一个意外。
她如一道破晓的曙光,让早已习惯夜色的肖邦,再一次感受到了太阳。
他无法形容她,又似乎可以用一切描述她——
那只飞进他世界里的小山雀,是明媚的c大调,是生机和活力,是阳光下的坦坦荡荡,是可以真诚无愧、大声喊出的真实。
肖邦将自己埋进手心里。
就像她的钢琴声一样,欧罗拉对他的吸引力是不讲道理的,等他现的时候,他早已过界了。
李斯特说,他抨击她看不到自己,是他钻牛角尖,忘了自己的身份。
但好友不知道,其实他也是在恐惧——害怕弗朗索瓦·彼颂,比不上弗里德里克·肖邦。
没有人比肖邦更了解肖邦。
本质上,他就像花园里自嘲的那样,是个不完美的、甚至糟糕的男人。
“先生,请您嫁给——啊不,是‘请做我的未婚夫’。”
他错了,错得很离谱。
他的山雀小姐,从一开始,看到的人就只有弗朗索瓦——除开肖邦的光环后,如此普通的一个男人,没有神性,完完全全的人类心脏,会嫉妒,会失控,会懊悔,会心痛。
欧罗拉,如果你还能……还能怜悯、赦免一个傲慢的人。
请再给我一次,坐在你钢琴边听你演奏的机会吧。
我,想见你。
*
安亭街38号。
马车停在街边,肖邦却不敢下车了。
这个男人收回手,哆嗦着又缩进黑暗里。
要鼓起多大勇气,他才能忘记他刺出去的刺留下的伤痛;要穿上多少层盔甲,他才敢再一次站在她面前。
迫切地想见她,想和她说话,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想待在她身边。
只要,推开这扇门。
良久后,肖邦又颤抖的手,只打开了车窗。
太冲动了——他应该先回去写一封长长的致歉信,附上鲜花和致歉的礼物,然后再递上一张拜帖,沐浴打理好一切,穿上他最喜欢的那套衣服,再来见她的。
该死,他还能闻到自己身上隐约的酒气。
被挫败感压得不敢动弹的青年,小心地隐蔽自己,偷偷地扒着车窗向外看。
落地大窗的窗帘没有拉起。室内亮着烛火,但钢琴孤零零地立在那,琴盖关得严严实实。
她人呢?
肖邦不禁探出头,只看到佩蒂特在门口面色焦急地走来走去。
欧罗拉还没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