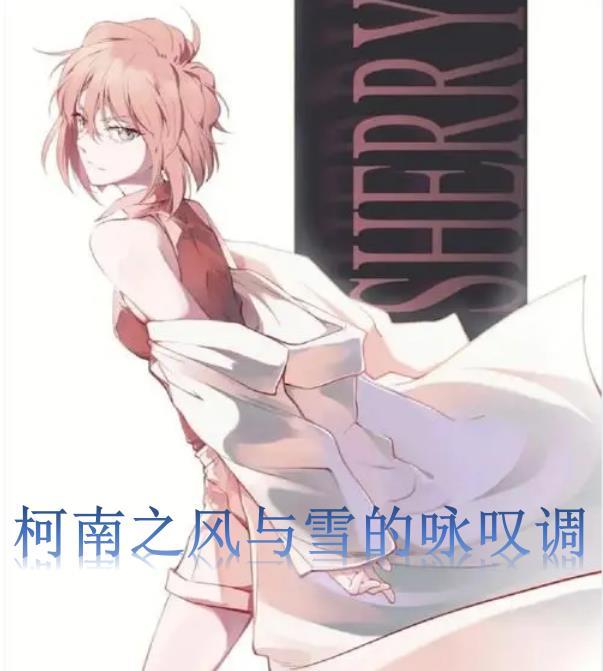69书吧>复苏越早存活希望越大是否正确 > 45 跟我回国 这不是世界的尽头(第2页)
45 跟我回国 这不是世界的尽头(第2页)
黎阳的泪水没有控制住,一直一直就在他的亲吻中流个不停。
“好久不见,我以为你见不到我了……对不起。”
她嘶哑却淡薄如雾的话像砂纸磨着复遥岑的心口。
他这一个月,每天都无法控制地在后悔为什么要让她答应不要出事,她如果不醒,他也要陷入在这个漩涡里悔恨终身无法自拔。
这一刻再听到她这话,复遥岑心脏像被狠狠抓住,鲜血直流,“是我不好,不该总让你保护自己的,我应该跟你说,在哪儿都不用怕,活着不能见,死了能见,不用担心我见不到你了,我无所谓,总能见到的,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换个世界见。”
“复遥岑。”
黎阳眼泪失控,情绪崩溃。
复遥岑拿纸巾给她擦,“不说了,别说,乖……好好休息。”
“玉磊哥呢?”
黎阳忽然想起来,眼神一变,明明没声音没力气,却努力问他,“那个,男记者呢?和我一起的那……”
复遥岑盯着她的唇,每一个字都尽力听明白了,他握紧她的手安抚她:“没事,没事,他醒了。”
黎阳舒了一大口气,又问:“庞大哥呢?”
“他也很好。”
黎阳点点头,好像全世界的重量从身上卸下去了,此刻身上再怎么痛也无所谓了,他们没事就好了,其他有什么所谓呢。
她体力透支,额上浮起一层细汗,脸色苍白,紧闭的双眸仿佛刚刚那场对话像梦一样,她还在深度昏迷中。
复遥岑给她盖好被子,找医生给她做检查,他就站在几米之外,不敢再靠近,好像一靠近就夺走了她的精力,她没法好好休息。
事实上她这一场苏醒确实像假的,这一天过后,她连着又陷入好几天的昏迷,一直没醒。
四月十九号,距离那日第五天,她出事的第三十五天,她总算第二次苏醒。
复遥岑能感觉到她上一次醒来得到了安好的消息后,似乎精神松懈了下去,后面几天恢复得很快,脸上的血色在一点点地浮现。
黎岸生在黎阳第一次清醒时虽没和她说过话,但是确认她基本已经生命无虞之后,他启程回国了一趟。
回去两天,办完事就从国内沿着迪拜的航线再次回到西亚。
不巧,这次他到时听说黎阳再次醒来,但他去探望时她在睡觉。
两次没有说上话,黎岸生望着病床上呼吸单薄好像随时要消失的女儿,忽然觉得是命的事,两次了他都没见到她。
他转头和复遥岑说去聊一聊。
复遥岑在独立的病房中坐下后就拿起报纸翻看,一个绑架案折了新云网的三个得力干将,三人都基本无法再继续这份工作,新云网气得连月来已经发表了数篇国际文章谴责极端组织残害战地记者罔顾国际规则泯灭人性……
黎岸生坐在对面沙发,和上一次一样。
看了看女婿平静疏冷的模样,黎岸生知道,复遥岑明白他要说什么。
所以他就直说了:“我问了,她是说没有,我查了,是有,没错,”
他声音沉重,“那晚我应酬喝多了,在休息,她接了电话。通话记录里,对方说他们在西亚,绑架了记者黎阳与她的同事,需要立即打赎金来赎人。”
复遥岑眼神定格在报纸上她的名字上。
黎岸生声音沙哑:“她犹豫了两秒钟,说打错了,就挂了。”
复遥岑捏紧手。
纸张用力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病房中清晰可闻,黎岸生看着他的动作与脸色,神情愧疚道:“我已经回去找她了。我知道还是太晚了,是我对不起黎阳。”
复遥岑:“您对不起她的多了。”
黎岸生定定看着这个向来对他尊重有加的女婿。
复遥岑目光圈绕着报纸上黎阳二字,眷恋描摹,没有移开一分:“您都不知道,她选择这份你一直不支持的工作,是为了远离那个所谓的家。”
黎岸生眼神闪动,眸中飘着深深的意外。
复遥岑:“您也不知道,她当年千里迢迢跑去锡城找我,求我别解除婚约,是她不想回北市去毫无意义地过一辈子,她想去做一份让她觉得活着也算有意义的事,哪怕死在这里也比在北市那个家里要快活。”
黎岸生呼吸凝滞,神色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