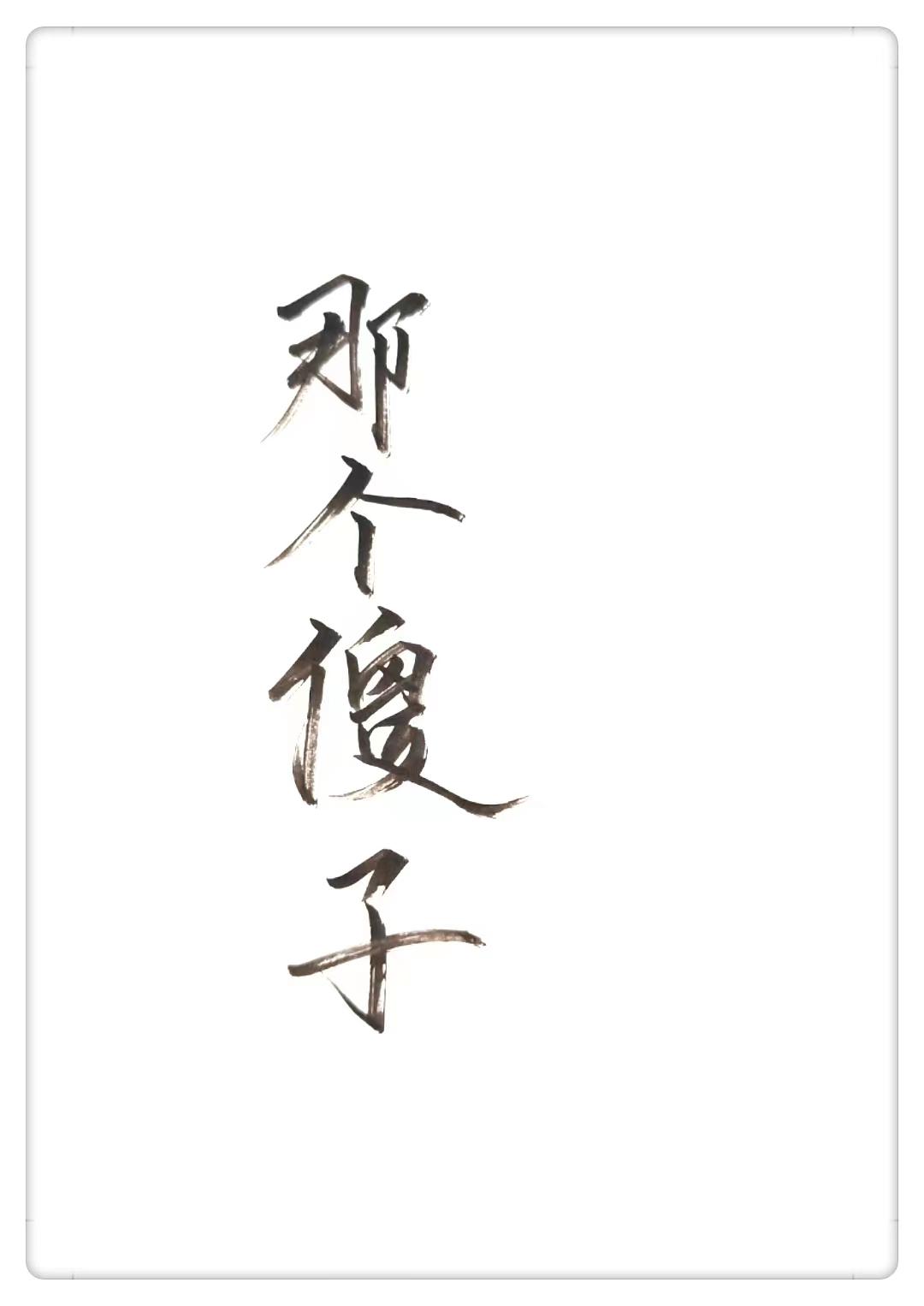69书吧>鬼推背的解释是什么 > 第七十三章 最完美的祭品(第2页)
第七十三章 最完美的祭品(第2页)
有子女儿媳责打辱骂,老人逃无可逃,在家暴中出绝望压抑的痛哭哀号。
有男人不堪病痛折磨,他人嘲笑,在病**上出歇斯底里的哭喊。
有在新欢阴测测的笑声里切腕自尽,却哭到昏天黑地、肝肠寸断的女人的叫喊。
甚至隐约的,可听到有人的身体重重摔跌在地上的声响;有骨骼破碎时的脆响;有伤口崩裂的声响;有血液从创口处汩汩流淌而出的声响;有细胞病变时出的不可思议的声响;有整个世界在裂变,在破碎,在毁灭的一切声响……
渐渐的,我感到胸口那阵极沉重的压抑之感再度袭来。只是这一次,它们仿佛已不是来自外力。
我转身去看耗子,“老冯……我……我有点撑不下去了……”
可耗子仍在一根接一根的抽烟,脸上神情看来,并不见得比我冷静。
我挣扎着转身逃出了院子。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这哭声喊声叫骂声,始终如影随形。
在这片混乱的音声之中,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对我说:“好了,别Tm强撑了!你就是再假装活得人模人样,最后还不都要涂脂抹粉钻到地底下来,灰头土脸的一个人睡上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永永远远的睡下去,再也醒不过来……醒不过来了……”
我尽量不去理会这个声音,只是拼命往前奔逃。
我知道自己依然陷在那个诡异的“鬼打墙”
迷局中,根本逃不到任何地方去。
可我还是不停步的往前逃,仿佛只有不停的运动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才能将那些关于生命走向死亡的每一个细节和真相,远远的抛在脑后,抛在我不必去理会,不必去在意的那个黑暗而阴冷的地底世界中去。
可最终,我还是感到筋疲力竭,于是再次回到起点和终点处的董家小院之中。
耗子仍在一根接一根的点着烟,只是神情看来,似乎已经平静了许多。我无力的走过去,夺了一支烟在手里,凑着他的烟头点着了。猛吸一口,立即呛得一阵猛烈咳嗽,但同时,却忽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是的,在这阵久违的人间烟火里,我感到了片刻的轻松。
但是很快的,那些哭喊之声再度响起,我站起来,又想逃了。
耗子扯住我衣角,“够了!老刘,别再逃了,事实上你也无处可逃,我们都无处可逃。”
“那怎么办?”
我声嘶力竭的对耗子吼道,“他们这么折腾,你跟我也迟早被逼得自杀!”
耗子摇摇头,“没人逼我们。鬼灵有自己的世界,它们现在这样,只是在本能的诉说着自己走向死亡的每一个细节和真相。”
“那……那怎么办?”
我近乎求助的看着耗子。
“没别的办法,只有倾听。”
“倾听?”
“没错,倾听。倾听它们口里的所有真相,然后接受。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不必逃,永远都不必再逃了。”
我当然知道耗子说的有理,可我还是无法做到。
那些凄厉、绝望的音声,何止是在诉说各种死亡的真相,那简直就是在向你描述整个作为黑暗地狱的人间的真相。
那一刻,我宁愿这就是些冤死之后,随处躲于门后、山里、坟头上,等着吓吓胆小之人,或者掐死一二个替死对象,然后做阴森森状还魂的鬼魂。
可是,目前徘徊在眼前的这些,它们显然对于吓人一事毫无兴趣。
基本上,它们根本就无视你的存在。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自言自语,用一种近乎鬼意的诗情,表述着它们对于生命,对于死亡的种种看法,然后让你不断反省出你的生命其实根本无足轻重,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在鬼灵面前,在人类以外的天地万物之前炫耀的资本。因此,在死亡的庄严与肃穆面前,你活着才是真正的绝望,才是真正的悲剧,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悲剧。
我无力的问耗子:“你刚才在摄像头里,看到它们没有?”
耗子摇摇头,依然靠在土墙上静静的抽烟。
“那你是见到睡梦中的韩可生梦魇,意识到不妥,立即走出房间,才见到院子里不可思议的一幕?”
耗子又点点头,同时疲倦的叹了口气。
我完全无措了,“我怎么感觉,目前韩可的情形,好像比当初蒋欣和梁雪,还要严重许多倍?”
耗子语音低沉:“因为她比她们任何一个人,都更紧接完美的祭品啊。”
“祭品?”
我心里“咯噔”
一下,虽然每次听到新娘被送进这间洞房,我头脑里也会闪现出这么个词语,可那毕竟只是一种譬喻。然而此情此景之下,再听耗子这么说,我心里忽然浮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耗子又将一根烟放在了身旁,语气完全平静下来,“其实我们早该想到,这确实就是一场古老的祭祀仪式,一场历经无数代人,却被传承得已经面目全非的古老仪式。”
听耗子这么说,我本能的转过头去,看了一眼躺在洞房里的韩可,以及依然徘徊在房间外面的那些鬼魂。
“祭祀仪式?你是说,这个可怖风俗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古老而神秘的祭祀仪式?”
耗子想了想,“古老,但并不神秘。其实,它应该就是曾经广泛盛行于远古时代的一种关于**崇拜的祭天仪式而已。”
(未完待续)